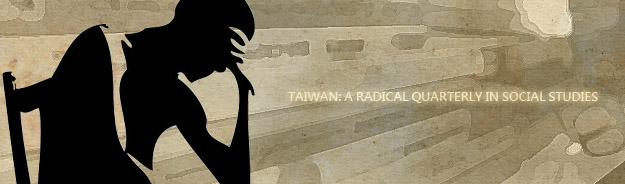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45期:
編輯室報告
科技從來就是社會性的;它在社會脈絡中發生,在社會脈絡中應用,在社會脈絡中爭議。關於這一點,從工業革命之初以砸毀紡織機器作為社會保護運動的英格蘭拉戴特(Luddites)激進份子、十九世紀末風雲際會歐陸的「科學社會主義者」、二十世紀初美英的「第三條路」(via media)進步運動者、二十世紀末印度的人民科學運動者、新興的STS(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者,到今天台灣社會的「反反盜版」運動者、性解放運動者……,是有一個基本的理解的。我們可以說,儘管他們的政治光譜殊異,儘管他們企圖介入科技的方式與目的大不相同,但對於科技是社會的也是政治的這個基本態度是相類的。科技的意義從來不只是限定在工業技術與利用厚生的範圍內,它直接捲進並構成現代社會的自我理解與定位(例如理性主義世界觀),更經常內延到正當知識模式以及存在意義與方式等知識論、倫理學與本體論問題。凡此不僅是學院問題,更是尖銳的政治問題。歷史上,關於科技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的尖銳政治(思想)鬥爭往往表現在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後進國(例如二十世紀初德國威瑪時期準納粹的「反動現代主義者」,中國以及其他傳統文明的「西化」與「傳統」的鬥爭)。好或不好,這種大規模的關於社會方向性的鬥爭於今似乎已大致偃息,但是在過去這一、二十年裡,關於科技與社會之間的緊張性,似乎又以新的方式、新的邏輯開展出來。一般說來,這基本上是由於新科技(特別是和人身、人倫、生活方式、環境有關的那些)的持續加速問世,從而使社會面臨被迫快速理解與應對的情境。這類科技危機與風險往往是空間上高度擴散,而且在科技先進與後進區域之間也幾乎沒有什麼時差,雖然不同社會與人群在產生有識反應的能力上有差。我們可以說新科技在快速地、差別化地、對不同的人群進行「傳統化」。能夠「現代」,就得靠培養不停面對新情勢的挑戰的本事,而且挑戰是不可預期、沒完沒了。
重新檢討當今的科學、技術(或科技)的社會性質與社會的科技性質,以及更重要的,在今天的台灣,我們該如何面對各種新興科技所帶來的挑戰?這個挑戰的性質為何?誰能(或應)面對這個挑戰?有效面對這些挑戰的基礎與策略為何?這些關心是《台社》籌畫這一期「科技與社會」專題的立意所在。
本期收進了四篇論文,其中包括一篇評論論文。吳嘉苓與周桂田的論文是以歷史與經驗資料為基礎的研究論文。雷祥麟與陳信行的論文則分別主要是關於社會議程(agenda)的訂定與理論爭議的反思。讀者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從任何一篇論文開始。在這四篇論文裡頭,雷祥麟的論文由於企圖大開大闔地指出一個科技典範的劇變,以及在此劇變前提下各種社會群體(特別是STS研究者)該當訂立出什麼社會議程,因此帶出了一些重要的提法,以及召喚出一些爭議。這篇論文或許值得首先介紹,因為它對我們下面的討論有幫助。
雷祥麟〈劇變中的科技、民主與社會:STS的挑戰〉一文的基調是樂觀昂揚的,指出自八0年代末期開始,科學知識的生產,走出了學院象牙塔,走進「社會」,並開始和應用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個「劇變」表現在制度上是大學與產業間的柏林圍牆應聲坍塌,表現在資本主義生產上是「技術化的科學」與「知識經濟」的狐步共舞,表現在知識(論)上是「再現的科學」以及實在論的三振出局。雖然雷祥麟也指出了這個劇變的核心構成之一是「科學知識的商品化」現象,但他認為,相對於過去(在知識生產與應用之間)的「隔絕體制」,把科學供在高不可攀的知識神殿,不食人間煙火、不理人間鬥爭,現今科技與社會二者之間重新相互穿透的新形勢,反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促使科技政治化的契機——因為科技走入社會,所以它就要付出神秘面紗被摘下的代價,必須要面對正當性的問題。在這個情境下,有三種群體可望積極介入這個劇變:科技專業社群、科技公民社會群體、以及STS研究者。雷祥麟的期待,好比說對STS研究者,是他(她)們應該要從如今已失其鹿的(建構論的)批判取向中撤出,轉進和「知識經濟」結合,從而「主動探索哪些『社會脈絡與價值』當被及早納入知識生產過程中」。唯有不避作為知識經濟的應用諮商者角色之嫌,STS才能獲得「深入敵營、入室操戈、甚至轉化對手的新可能性」。
雷祥麟這篇論文的核心企圖是為STS釐定它在當代的社會議程,因此它的最重要的意義之一其實是在於開放爭議這個議程所釐定的大方向。首先,對新科技的「社會性」的評估其實是可以爭議的。科技走下了研究大學的高閣,進入到社會,但這個社會指的是什麼?社會和產業(或經濟)在概念上是否要區分開來?以及,「社會」是否總是要加以階級的、性別的和其他的分疏?吳嘉苓的論文其實也間接地指出了科技與泛社會之關係的提法有其遮蔽性——假如「社會」沒有充分地被性別化和歷史化的話。其次,新科技是否真的比舊科技更對社會力量開放?科技保守派關於科學體制的自然化神話固然可說是反民主的,但這並不能馬上導出「去自然化」(意指「市場化的」)新科技是較民主的推論,畢竟,去自然化並不保證重新政治化與激進民主化。但雷祥麟似乎認為新科技與民主化之間的正向關連毋寧是更為明顯的;他認為商品化了的新科技和民主化之間是有一「健康的緊張關係」的。這個評價性意見其實也是可以爭議的。我們可以問:到底,新科技會結構性地提供了新的公共參與和「審議民主」的內在紋理養分,還是說新科技的新危機(例如各種生態與社會排除危機)要求人們進行反抗?換句話說,與知識經濟勾連的新科技真的正面地提供了科技民主化的沃土嗎?說到這裡,那第三點就牽涉到作為一種社會實踐的STS的安身立命的問題了。雷祥麟認為面對新的挑戰,批判的STS可能要讓位給在知識經濟中實作的STS。但如果前面兩個議題還是有爭議性的話,那麼這個關於STS的知識的社會角色的問題可能也還是高度開放的。STS似乎和當代社會中的其他知識派別並無二致,存在的意義並沒有客觀歷史或社會結構擔保的特權。面對「新自由主義共識」、「新經濟」、「知識經濟」、以及日益商品化的科技知識生產,STS研究者是否也必須要費勁兒地找到他自己的社會立場。雷祥麟對STS在知識經濟中應扮演何種角色的立場似乎處在一種兩難中,一方面,知識必須成為生產力,STS也不例外,但另一方面STS似乎又要扮演身曹心漢的艱難角色:「深入敵營、入室操戈、甚至轉化對手」。為何知識經濟是「敵」,其實需要被論述。轉化對手如何可能,這也可以爭議。但似乎更值得爭議的是:我們要轉化對手到什麼方向?這是一個最關鍵的問題,也是雷祥麟一文所關係到的最重要爭議之一,因為它直接聯繫到我們如何看待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霸權的無上律令——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問題。
陳信行的評論論文〈「科學戰爭」中的迷信、騙局、誤解與爭辯〉,藉由對最近在台灣翻譯出版的兩本批評STS的外文著作的內、外部評論,指出了論戰中的認識論問題,以及相關的種種政治與社會議題。其中一本是曾經大鬧文化研究與STS的「索可事件」的索可所參與著作的《知識的騙局》。不同於一般文化左派對索可的極端啟蒙主義與科學主義的刻板印象,陳信行所再現的索可以及《知識的騙局》則反而是支持STS關於科技與社會關係的大多數基本論點。這使得陳信行從而宣稱STS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的必要性已經不是問題了。但是,以一個STS的支持者與工作者的角度,陳信行反身地指出索可對STS的一個批判的有效之處,而此一批判竟然是指STS知識傳統有嚴重的「科學主義」問題!這從何說起呢?STS不是和眾多文化轉向後的研究領域一樣,是一個堅定的建構主義與認識論相對主義的支持者,並據此批判啟蒙主義與科學主義嗎?
對索可而言,STS從「強綱領」開始、到「實驗室研究」、到「角色網絡」的一系列發展,都和一種實證主義的科學觀甚為親近。後者的最重要特徵就是將經驗世界進行學術切割,從而將研究對象置放於一個可以用經驗資料說明證立的,從而可說是按照方法論的要求所圈定的範圍內,從而放棄了對更廣泛的社會關係的關注,並放棄了對社會整體性的研究承諾,而這和STS所從生的「1960年代批判質疑的時代精神」產生了不調和狀態。例如,Latour的「實驗室研究」,對索可以及陳信行而言,雖然成功地在微觀社會與權力層次上說明了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性質,但代價則是對更廣的整體性社會關係脈絡的切割。我們把索可/陳信行的這個對STS所潛藏的科學主義的質疑,以及對STS社會批判和社會解放運動角色的立場認定,和雷祥麟關於STS應該主動進入到知識經濟的科技生產過程中的立場,進行一個對比,似乎可以看到非常不同的對於STS的社會定位。這些或許都是往後探討科技與社會的問題時可以深化的爭議。
要瞭解實驗室,必須要瞭解實驗室之外的「大社會」。陳信行把這個批評立場自反地應用到對「科學戰爭」本身的理解:要理解科學戰爭嗎?那你得從經院出走進入現實。他認為建構論和實在論、後現代派和「啟蒙主義」、多元差異和團結行動……在理論上的對立(而這些對立多少都設定了STS的主調以及「科學戰爭」中的煙硝)都隨著現實情勢的轉變而平息。這個新現實情勢的最大例證,根據陳信行,就是鳴放於1999年西雅圖的反全球化運動,這個運動體現了「尊重多元差異的團結行動的確是可能的」。陳信行關於這個西雅圖「劇變」的提法是可以爭議的,就像雷祥麟關於「三螺旋鍊」或「模式二」或「知識經濟時代」的提法是可以爭議的,是一樣的。但這裡更有趣的是,他們兩位都不約而同地(誠然以相當不同的理由),取消了「科學戰爭」的學院爭議的優先性,不認為於今關於實在論或是建構論孰優這個老問題還有啥好談的,也都不約而同地指出這些學術爭論的脫離現實,而差異僅在於,對雷祥麟而言,這個現實是知識經濟的興起以及STS(在無可選擇下)的順勢而為,陳信行則恰恰採取對立的立場,這個現實是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全球運動。這或許是關於STS在當代位置角色的最核心爭議,但迄今為止惜乎尚未上升到理論與政治高度。本期雷與陳的兩篇論文或許有助於深度爭議與辯論的開展。
這個專題有兩篇經驗性研究論文。吳嘉苓的〈台灣的新生殖科技與性別政治,1950-2000〉一文,一路追索五十年來助孕科技和台灣社會中的性別政治之間的糾葛纏繞。吳嘉苓揚棄社會或科技的決定論,採用「社會科技聚合體」這樣的一種社會地景觀,體察兩者「相互滲透的樣態」。因此,她一方面考察助孕科技對性別社會的影響(例如醫療的性別不均等入侵、親屬關係與血親觀念的轉變、與生殖的性別分工等等),也同時考察性別社會的規範與慣行如何影響助孕科技的發展與應用。科技與性別政治在不同歷史階段中的多層複雜關係,不是任何單一解釋模型(例如理性行為)或是單一評價模式(父權社會的再生產)所能完全解釋的。例如AID(由捐精者精子完成的人工受精)在70年代被大量採用,但在90年代則幾乎銷聲匿跡,並為ICSI(卵細胞質內精子顯微注射)取代。儘管後者的懷孕率遠遠低於前者,但就是因為「男性的種」的舊觀念再度被用來和新科技結合而使它得到發展機會,這效果上使得70年代一度淡薄的血親觀念與男性留種觀念再度因新科技而上揚,並使得女體再度暴露於高度醫療入侵下。這是新科技的問題,吳嘉苓不否認,但她也同時指出支配性的社會價值觀也在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為主流社會價值把血親擺在優位,把「減少(對女性的)侵入性醫療干預」視為末節,所以才不會實現「領養優於AID,AID優於ICSI」的社會踐行,反而是倒過來幹。但同時,助孕科技也不可簡單地視為父權社會的函數反映,畢竟科技也是「行動者」,也能夠影響性別社會的結構與邏輯。吳嘉菱就指出,新生殖科技(例如AID)能夠使獨身女性或是女同志能夠不必進入到異性戀關係,就可以藉由新科技達到懷孕目的。社會與科技的確來回交互影響,而其中社會的歷史性與科技的異質性必須要被細緻的審視:科技與社會均不能被拜物教化。
這一篇既對生殖科技本身的內在異質性又對歷史脈絡的差異性保持高度敏感的研究,不但把女性主義文獻關於生殖科技與女性主體的討論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也為我們把台灣社會裡的性別政治開了一扇新窗。透過這扇窗子,我們看到女體被生殖化與醫療化的複雜歷史面貌,看到眾多男性在這個過程中覺醒的遲緩,看到新「醫療助孕的社會」的到來,於其中,女體與生殖之間的關係再度被套牢。這個研究雖然沒有直接碰觸到經濟體制與階級差異的面向,誠然也無法要求一篇論文面面俱到。但是整個對女體進行科技殖民的背後龐大「知識經濟」誘因(ICSI對醫療部門的利基大於AID,AID大於領養!),以及社會不同群體進入「醫療助孕社會」的成本與機會的差異(如果有,是否牽涉到「社會正義」的問題?社會正義問題和規訓社會的問題意識是否互斥?),恐怕都是可以從目前這個研究拉出來的一些想像。
周桂田的〈在地化風險之實踐與理論缺口——遲滯型高科技風險社會〉探討了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在高科技風險的全球化流竄中,台灣社會如何面對這樣的挑戰?在這個必然是屬於「全球在地化」的風險運動中,什麼原因造成了台灣社會的反應遲滯?周桂田從GMO(基因改造食品)在台灣只遭遇到低度爭議的這個現象出發,具體地回答上述問題。
除了美國以外(因為是GMO成品與技術的主輸出國),全世界的資本先進國,在反對GMO的運動上都有甚為可觀的發展,培養了為數甚夥的社會運動團體以及科技公眾的出現,從而拉出很多問題的深入討論(例如人口問題、南北問題、科技自然與社會之間的道德與倫理議題),但在台灣,這樣的議題卻非常的冷。偶在媒體炒作之下,民眾有了恐慌但卻沒有成為議論,遑論形成公共議程。這是怎麼回事呢?周桂田繼他在《台社》39期的〈生物科技產業與社會風險〉一文後,繼續討論同一個問題。在前文中,周桂田經由對國家科技官僚的分析,指出政府的不行動造成了「遲滯型高科技風險社會的出現」。本期的論文則是把分析視野從國家移至社會本身:媒體、社會運動、與市民社會。周桂田的核心起訴對象是台灣的社會性質:缺乏一個成熟的公(市)民社會;一個「鑲嵌在政治文化上的公共理性辯論傳統的相對匱乏」。因為這個根本的原因,台灣的社會運動以及媒體陷入到一種膠著的、遲滯的、缺乏批判理性的情境。姑不論這樣的一種「公民文化主義」的論斷是否過於符合學界常識,以及是否有套套邏輯之嫌,周桂田之文的確(透過經驗資料)具體地、精彩地勾勒出台灣的媒體以及社會運動被上述台灣社會性質所構陷的尷尬狀態。
眾媒體對GMO風險的報導竟都一面倒地不是抹粉GMO或生物科技,就是宣揚個人化的避險手段(例如標示義務),相較而言,對這個問題進一步政治化與公共化的討論(例如關於進口政策)則是鳳毛麟角。這和歐洲(好比德國)媒體公眾的關切重點是大相逕庭的。而媒體的這種價值層級又和消費者運動的個人主義色彩有密切關係,例如,首先議題化GMO的「環品會」就強調從消費者個人的抵制(理由:沒人吃,就沒人種),而非從公共政策辯論入手。媒體與運動團體因而都可說是「風險個人化」的催生者。
當然媒體與運動團體的反應「遲滯」和它們必須辛苦地從無到有補足知識落差有關,但周桂田指出,更關鍵的還是在整個市民社會的體質孱弱,而後者又和整個台灣社會竭神殫精地投身到國族主義神經戰上有關。這一切使得社會落後於風險現實,形成周桂田所說的「系統落差」。在此落差下,社會、國家與科技產業的自我宣傳三者之間處在一種沒有內在緊張的狀態;新的生物科技不但變成了國家官僚的發展方向,更成為了社會的普遍信念,因為它是進步與發展的同義詞。這讓我們想到雷祥麟關於STS的角色的討論,認為STS應該「深入敵營、入室操戈、轉化對手」,其實是有直覺合理性的,值得被深化討論。
科技拜物教在台灣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這從一般人對科技效用的崇拜以及對科技夾槓的敬威,就可略窺一二了。科技與社會其實並沒有西方文獻中所經常預設的緊張關係。這當然可說,如周桂田,是一個弱化的市民社會的展現,但也未嘗不是一個弱化的「神聖社會」的展現。陳信行在他的論文結束前,提到印度教基本教義派的政黨對批判的世俗主義的否定態度;質疑科學、啟蒙、世俗政治、商業、與市場。這種反科技拜物教的態度固不足取,但恰如陳信行所點出來的,這種態度在「宗教虔誠度普遍不高的台灣」也是罕見的,而「比較常見的反倒是犬儒功利的態度」。這麼說來,缺少(基本教義派與「科學」之間的)超越主義價值對決反而是台灣的福份,台灣社會的前途(如就科技與民主而言)可能還真的需要從這高燒(hyper)世俗的、功利的、個人主義的、科技崇拜的、發展主義的「理性文化」著手,進行內在批判與改造,在接受某些現代性的前提(例如社會運動、民主、多元)下,進行對現代性的激進改造。科技與社會的關係最後還是得落實到民主的問題意識上。在這一期的專題基礎上,《台社》期望這個科技、社會、民主、與現代性的討論在將來繼續深化。
本期有兩篇回應文字。頭一篇是王思睿與何家棟的〈新威權主義與新左派的歷史根源〉。這篇文章是回應《台社》42期汪暉的〈「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及批判〉。這篇回應文章和汪暉的論文之間的主要爭議在於:中國大陸1989年運動的歷史定位問題、當今「真正的」強勢話語為何的問題、「新自由主義」該當如合理解的問題、「自由」與「平等」之間的關係的問題、以及「民主」當如何被理解的問題。對王思睿與何家棟而言,九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最強勢的話語系統是一個由各種保守意識型態構成的策略聯盟,可名之為「新威權主義」。面對新威權主義這個敵人,社會批判的能量其實現實地也僅能以反特權、爭自由為目標,平等問題至少暫時還無法排入議程,並且因為關於它的爭議在進步批判陣營中所造成的分裂性,因此還應該暫被懸置。將王/何之文與汪暉之文合而讀之,除了可幫助讀者進一步熟悉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對於情勢的爭議外,也更可以幫助這個區域的批判知識份子對一些核心的價值與實踐問題,作進一步的反思。在「全球化」的年代中,把區域範圍內其他知識界的活動當作「有意義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成為我們參照、反思、與溝通的基礎,是需要我們繼續耕耘的。
這一期的第二篇回應文字是瞿宛文的〈反全球化的意義何在?〉,回應《台社》44期趙剛的〈為何反全球化?如何反?〉。後者質疑以瞿宛文為代表的修正學派著重在國家與發展的問題意識可能會妨礙它有系統地討論平等和環境的問題,以及批判地討論國家在這些問題上扮演的角色。瞿宛文的回應雖然是在直接回應這個質疑,但其實已經逸出了對趙文的「回應」規模,而幾乎是她對於全球化問題的一個簡約但清晰的縱述,這對於深化目前關於全球化的討論有一定的幫助。《台社》鼓勵這樣的對話。
瞿宛文心目中的「反全球化者」(anti-globalizer)其實主要是美國的大工會以及某些政治經濟學左派。這些人,根據瞿宛文,以一些自利的動機或是似是而非的說法進行反全球化,這些說法包括「往下看齊」(race to the bottom)、工資是競爭力的最重要甚或唯一的指標、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鐵律、藍色(勞動)以及綠色(環境)條款是對第三世界的正義干預……等等。瞿宛文呼籲在地的進步人士不可隨著這些「反全球化者」起舞,因為:一、美國工人失業不是東亞勞工該負責的,先進國與後進國的勞工並不曾真的處於競爭關係中;對於美國低教育水平者的勞動條件的下滑,美國的國家要負責,美國的左派應在國內範圍要求落實社會民主;二、藍色與綠色條款是意識型態、必須以其實際捍衛的特殊利益考察之;三、全球的勞工以民族國家為單位進行競爭是一個現實,談勞工問題不可視而不見。瞿宛文認為在地的左派或進步人士不應也不可能要求先進國的資本不外移,應該做的是責成國家(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將勞動力升級的成本社會化;而這在自由化最徹底的美國是由個人自行負擔的。因此她堅持:「鬥爭都還是主要是國內的,最主要的是要反對國家或資本,以全球化意識型態、以全球化趨勢作為藉口,來壓低工資與勞動條件,來降低各種社會條件。」
瞿宛文的很多論點其實和趙剛在44期的「反全球化」觀點並沒有重大矛盾之處,至少,他們都反對市場的霸權統治、反對美國霸權推展「全球化意識型態」、反對全球化作為一不可逆轉的趨勢的宣傳、反對所謂民族國家式微說。同時,他們都贊成國家的相對自主性,也都贊成左翼與進步人士的最重要的作用空間之一是在民族國家這個尺度上,也都支持(布迪厄的)國家「左手」說。
瞿宛文的文章曾稍稍觸碰,但沒有機會直接深入處理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兩岸關係以及台灣所佔據的資本輸出位置。面對中國大陸(當然還有尼加拉瓜及其他!),台灣是資本輸出國。台灣的進步論述要如何面對這樣一個台灣在全球化中的雙重身份,恐怕給我們增添了一個新的複雜向度。當然,台灣對中國大陸也並不僅只是單純的資本輸出的關係,大陸也向台灣輸出。近來最具爭議性的大陸進口物品之一就是大陸書籍。如何在全球或是區域經濟的層次上看待這個問題,是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但是當局粗暴查扣大陸書籍的作法則是一個再單純不過的侵犯言論與學術自由的問題。問津堂事件暴露了國家機器在處理這些新興議題上的無厘、無理與無禮,使一個原本可以打開公共論述的議,被矮化成國家暴力的對象。《台社》一葉知秋我心憂之,深感必須發聲,因此由本社編委草擬反對聲明,隨即進行抗議連署活動。這個活動的〈聲明〉以及連署名單現附在本期末尾——也算是留存一份歷史見證吧!
「科技與社會」專題
台灣的新生殖科技與性別政治,1950-2000/吳嘉苓(45 民 91.3 頁 1-68)
本文分析人工協助生殖科技過去50年在台灣的歷史發展,探討不孕診療在什麼樣的異性戀父權社會下發展,新生殖科技又如何可能改變生殖理念與實作,挑戰生殖分工,撼動性別系統。我們發現,50年代男性遠生殖的生殖理念,使得不孕檢查重女輕男;重視父系傳承的社會價值,也使當時對於AID的討論著重在男權的保障。然而,在70年代開始,強調男女同步的不孕檢查,將男性拉近生殖,而AID增高實施比例,降低「男性的種」的重要性,造就非父系血親的生殖突破。90年代,不孕檢查逐漸破除「生殖=女人」的生殖意識,但是以IVF與ICSI為主的助孕科技反而由於「男性不孕,治療女性」的不孕醫療模式,強化了女體與生殖的關連性。雖然異性戀夫妻的不孕「治療」愈發以血親為重,非異性戀婚姻體制的邊緣他者卻在90年代開始利用新生殖科技其分離性與生殖的特色,成為使用科技的新主體。現今醫學凝視的對象也從不孕的器官擴散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醫療助孕的社會儼然來臨。本文強調,著重新生殖科技多重使用的歷史脈絡與意義轉換,以及掌握性別與生殖關係的多樣性,才能明辨新生殖科技與性別系統的變動關係。
關鍵字:新生殖科技、性別、不孕
By means of investigat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NRT) in Taiwan since 1950s, I demonstrate how the heterosexual patriarchy shapes the medical treatment of infertility, and how the NRT could transform the sex/gender system. In the 1950s, the reproductive ideologies that equated women with procreation exempted men from infertility examination and treatment. In the 70s, the emphasis on the couple as a unit for infertility exam, as well as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using donors' semen, challenged the orthodoxy of husbands' lineage. However in the 90s, while the voice of "men first" in the infertility exam further linked men with reproduction, as the NRT advanced, women had to experience more and more intrusive medical intervention. Particularly, with the availability of in-vitro fertilization and ICSI, fertile women with their infertile male partners often had to undergo more medical intrusion. While the heterosexual couples tended to apply the NRT to the attainment of biological parenthoo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RT that separate heterosexual sex from procreation led single women and lesbians to use the NRT to have their own children. Also in the 90s, the medical gaze extended from the infertile bodies to various dimensions of social lives, thus implying the birth of a society of medicalized conception. This paper stresses that only by seeing the multiple meanings and diverse uses of the NRT, as well as the complexity of the sex/gender system, could we reveal the dynamic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NRT and the society.
Keywords: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gender, infertility, reproduction
在地化風險之實踐與理論缺口—遲滯型高科技風險社會/周桂田(45 民 91.3 頁 69-122)
本文將從比較的角度,分析德國與台灣媒體相關基因科技之「風險論述」,並配合特定歷史事件及脈絡,探討其相同及相異之處。同時,進一步試圖窺探相對於全球性風湧雲起反基因科技風險運動的發展,台灣社會所缺乏對高科技風險的警醒回應之因;以典型的在地化環境、消費運動而言,社會中的知識份子,尤其集中於都會中以知識菁英為領導取向的公民團體,經常是台灣生態、消費運動鼓吹、行動的主體(以同樣是高科技風險的核四案、拒煙案為例),因此,筆者的問題意識便是,為何面對基因科技(食品)所形成的在地化風險卻呈現出實踐的缺口,什麼是其系統性的原因?而其又鑲箝在何種特殊的社會關係和脈絡傳統?因此也檢討到了西方主流風險社會理論的解釋效度,反省其所產生的理論缺口。事實上,由此種在地化風險實踐與理論上的缺口,似乎可以理解到基因科技風險的複雜性遠高於它者,而此將導致後進國家遲滯型的風險問題更加嚴重。
關鍵字:風險論述、反基因科技、風險運動、鑲嵌、特殊社會脈絡、遲滯型高科技風險
This article will comparatively analyze genetic risk discourse in Taiwan's and German media by virtue of historical events and contexts. Meanwhile, the author asks what is the reason that Taiwan's society is still lack of response to high-tech risk in comparative of global ongoing against-genetic risk movement.
In typical local environment and consumer movement take the intellectual important role, especially the intellectual elite organized civil group are always the actor, for example in case of against nuclear high-tech risk or against smoking movement. Accordingly, the thesis is which systematic causes leads to practical gap of against genetic risk in local place, and in which particular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context it really embeds.
Therefore, it reflects th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effect and gap of western theory of risk society. Actually, according to the comparative reflective thinking abou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ap of local risk movement, we can deeply realize the very complexity of genetic risk causes more serious risks in the delayed advanced country
Keywords:risk discourse, against genetic engineering, risk movement, embed, particular social context, delayed high-tech risk
.
劇變中的科技、民主與社會:STS(科技與社會研究)的挑戰/雷祥麟(45 民 91.3 頁 123-172)
由台灣近年來層出不窮的科技爭議做為出發點,本文企圖說明三個相互支持的論點。
第一、科技與社會的關係已發生重大的變革,兩者正由傳統的隔絕體制與文化價值中釋放出來,發展出深刻的相互穿透,從而與過去兩百年的歷史形成一個深遠的斷裂。本文將指出一系列的結構性改變,包括國家、大學與產業間的三螺旋鍊(Triple-Helix)的興起,新的知識生產模式,「模式二」(Mode 2)的誕生,科學知識的商品化,科學實作與其知識論的轉化,以初步描繪這個逐步形成的斷裂與新關係。
第二、我們需要發展出新的思考架構以了解科技與社會的新關係,而不當將初生的新關係視為舊規範下的異常與病態。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能繼續將傳統「外在因素」的介入科技事務視為暫時性的「例外」「墮落」「醜聞」或「病態」,而期待它們會自行消失,而我們終將返回純淨無暇、客觀獨立的科技世界。相反地,這幾組結構性力量的匯聚,將高度壓縮科技在已往所享有的(相對獨立的)非政治空間,從而要求我們在政治上、重新構想科技、民主政治、和社會之新可能。
第三、在科技與社會的新關係之下,過去賴以將科技「去政治化」的體制、價值、與策略都將面臨巨大的挑戰,是以將引發一波「科技民主化」的問題與討論。更確切一點地 說,是科技內的民主(Democracy within Science )的議題。為了因應這個新議題,本文最後為三個群體—科學社群、科技公民社會、STS研究者(含人文社會學者)—來初步描繪在創造一個「民主化的科技」中,他們所面臨的挑戰、機會、以及當下可以從事的實驗。
關鍵字:科技與社會、科技公民、科技與民主
Starting from the rise of techno-scientific controversies in Taiwan, this essay intends to make three interrelated arguments. Fir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science and society has been going through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recent decade. Due to the conjunction of a series of social forces, the institu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will depart substantially from the insulationist model. Second, in light of this recent development, scholars need to develop a new framework in order to properly understand the scope and the implication of this emerging phenomenon. As techno-science is no longer perceived to be insulated from the society, techno-science will lose its status as a normative authority beyond politics and society. Third, as the result, we need to reconsid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science, democracy and society. To help bring out a democratic science, this essay concludes by suggesting a set of experimental conceptions and practices to tree relevant groups of people: scientific community, civil-technical group, and the STS scholarly community.
Keyword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 techno-science citizenship, techno-science and democracy
「科學戰爭」中的迷信、騙局、誤解與爭辯:評Gross & Levitt《高級迷信》與Sokal & Bricmont《知識的騙局》中譯本/陳信行(45 民 91.3 頁 173-208)
《高級迷信》與《知識的騙局》兩書的中譯完成介紹所謂的「科學戰爭」辯論到台灣所需的一半工作。這場熱烈的論戰表面上是關於科學與技術研究領域中的社會建構取徑的價值以及方法論/知識論相對主義的問題。它反映了冷戰之後、西雅圖事件之前美國學界高度焦慮的知識氛圍。然而,「科學戰爭」的影響超出了原來的戰場,在一些議題上引起了有意義的辯論,如:科學民主化的問題、美國左翼的戰略問題、以及後殖民主義把科學與「跨文化的真理」的概念批判為西方宰制的意識型態的問題。在兩本書中,《高級迷信》一再地使用稻草人攻擊而使得其論述品質低落;而雖然《知識的騙局》則是一個謹慎的防禦,集中在批評後現代人文學者誤用自然科學概念。Sokal & Bricmont 批評科學的社會研究之中有科學主義的傾向,本文從科學研究中圍繞著「強綱領」及其他社會建構派研究方案的辯論來討論,並發現這個批評具有一定的價值。
關鍵字:科學與技術研究、社會建構論、相對主義、科學哲學、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Gross & Levitt's Higher Superstition and Sokal & Bricmont's Fashionable Nonsense amounts to half of the necessary work for introducing the so-called "Science Wars" to Taiwan. This highly flaming debate, ostensibly on the validity of the social-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and the problems of methodological/epistemological relativism, actually reflects the deeply anxious intellectual milieu in the post-Cold War, pre-Seattle US academe. The ramifications of the "Science Wars," however, exceed the original field of battle, and raise meaningful debates on issues such as democratization of science, the strategies for the Left in the US, and the post-colonial critiques of science and the idea of trans-cultural truth as an ideology of Western domination. Between the two books, Higher Superstition is found to be of questionable intellectual quality, especially for its repeated use of straw-man attacks, while Fashionable Nonsense a more cautious defense against the misuse of natural-scientific language by the post-modern humanists despite the flamboyant image of one of the authors. Sokal & Bricmont's critique of scientificism in th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is discussed and found warranted in light of the history of debates on the "Strong Programme" and other social-constructivist research schemes in science studies.
keyword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ocial constructivism, relativism, philosophy of science, postmodernism, post-colonialism
議題與回應
新權威主義與新左派的歷史根源—評汪暉〈“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及批判〉/王思睿、何家棟(45 民 91.3 頁 209-246)
本文不同意汪暉將一九八九年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稱為“社會運動”,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是政治運動,是以“反腐敗”、“爭民主”為旗幟的對內的國民運動或市民運動,從運動主體方面來說,目標是爭取實現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等公民憲法權利。一九八年代大陸的強勢話語是新啟蒙主義或稱新啟蒙思潮。一九九年代的強勢話語則是反對新啟蒙主義的,在各主要領域均反其道而行之,穩定和保守無疑是它的基調。所以,現在大陸的強勢話語並非汪暉所說的“新自由主義”,而是“新威權主義”。新威權主義是一個理論聯盟,它的成員包括新保守主義、新秩序主義、新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等。在大陸官員階層中,新威權主義話語已經逐漸取代馬克思列寧主義教條,成為統治的意識形態。一九九○年代中國思想領域的爭論焦點並不是《再論》所說的“自由與平等”問題,而依舊是“自由與特權”問題。這使人們產生出一種希冀:中國自由主義和“新左派”保留在平等問題上的歧見,首先在自由與民主問題上達成共識並結成統一戰線,形成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不分左右)與反自由民主勢力的對壘。
關鍵字:新威權主義、自由主義、新左派、自由、民主
This article rejects Wang Hui's naming of the Chinese mass movement of 1989 as "social movement." The movement of 1989 was a political movement characterized by broad appeals of "against corruption" and "for democracy." Constituency-wise, the movement was a citizens' movement. Goal-wise, the movement was geared to realizing constitutional rights, e.g., freedom of press, freedom of association, etc. This article also disagrees with Wang Hui's labeling of neoliberalism as the dominant discourse in post-1989 mainland China. While the dominant discourse of the 1980s was the new enlightenmentism, the post- 1989 dominant discourse has been new authoritarianism which goes squarely against the new enlightenmentism and claims for stability and tradition in virtually all domains.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s an alliance of various theoretical strands, including new conservatism, new Law and Order, new statism, and nationalism, etc. Within the bureaucratic apparatus,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has, by gradually replacing Marxist-Leninist lexicons, become the dominant ideology. In this ligh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vital debat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political thought lies not in what Wang Hui took it to be the issue of "freedom vs. equality" but rather in the lingering issue of "freedom vs. privilege." An expectation is thus followed: Liberalism and the "new Left" in China should leave their divergence on the issue of equality aside for the moment and build up a united front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which sets itself firmly against the anti-freedom and anti-democracy citadels.
Keywords:new authoritarianism, liberalism, new left, freedom, democracy
反全球化的意義何在?—回應〈為何反全球化?如何反?〉/瞿宛文(45 民 91.3 頁 247-)
近來英美在全球強力推銷其以自由市場為主體的全球化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在諸先進國內,也興起了有廣泛參與的跨國性的反全球化運動。在此情境下,對身在台灣的我們,反全球化的意義何在?進步人士對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意識形態有共識,但是先進國內反全球化的運動,其實部分隱念了認為落後國家以低工資低環保標準奪走先進國工作機會的看法,這與事實並不相符,同時也意味著對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敵意,並具有反進步的意涵。台灣藉由參與國際分工而成長,快速的產業循環又意味著部份產業與工作的外移,處於中間位置的台灣,實沒有立場也不應接受先進國內反全球化運動這部分的說法。落後國家必須向先進國學習,又必須保持自主性才能發展,參與全球化本就是一兩難的處境。反對全球化意識形態、反對歐美主導的全球化之餘,我們是否也要反對全球化本身?這是個需要更多討論的難題。
Anti-globalization movement is all the rage in the advanced countries in recent years. Should the progressives in Taiwan join in this movement? The US has been trying to impose its neo-liberal version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rest of the world, which is opposed unanimously by progressives all over. Many anti-globalizers in the advanced countries, however, embraced the 'race-to-the-bottom' view of globalization and are hence hostile towar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aiwan achieved fast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ost-war period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global market. Swift turning of the industrial product cycles meant that many low-end jobs have been moving out of Taiwan lately. We should be sympathetic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elsewher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nd are really in no position to join those anti-globalizers in the advanced countr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