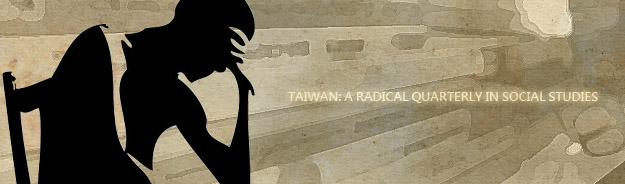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42期:
編輯室報告
上一期鄭鴻生的歷史報告——〈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透過對七年代初台灣左翼青年學生反對實踐的歷史回顧,為台灣左翼運動史中原先的一段空白補上人影聲音、為意義已被權力凝固的「反對運動」打開歷史熱流的閘門、為台灣島上素來缺乏理想主義的控訴提出有力抗辯。這樣的一個歷史報告當然不是為了趕「搜尋社區老照片」的流行,或僅是老軍憑弔古戰場,而是為了要拉出我們對於歷史的反思,以為今用。而鄭鴻生的精彩報告果然引領出精彩的(或至少是誠懇的)歷史反思。佇立在鄭鴻生所搭出來的歷史場景邊,呂正惠與錢永祥這兩位台社編委,以一種自覺的反傳記文學的方式,對那一段歷史的意義提出各自的興觀群怨。雖然他們兩位對那段歷史的認知與評價在很多方面或許迥異,但兩位不約而同地都對一根本之事發問——什麼才構成「反對」(或「左派」)?都試著提問為什麼六○年代與七○年代的反對(或左翼)運動遭到潰敗的命運?都殊途同歸地提出信念與認同和反對實踐之間的關係的問題。呂正惠認為台灣六年代以來的自由主義啟蒙運動或左翼思想運動不禁一擊的原因,在於忽視了中國這個「巨大的歷史現實」問題,沒有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思考中國與世界問題。言下之意,在台灣,「統」是「左」的必要條件。相對於呂正惠這種目標清楚的價值追求,錢永祥則相信(還可以用這個詞嗎?):「懷疑」是反對實踐的追求中不可或缺的構成部分。或許是來自個人實踐經驗之銘刻,或許是來自對上一個世紀全球左翼在理論、倫理與政治上的挫敗與質變的一體同悲,錢永祥指出,反對運動者在實踐當中,一定得戒慎地維繫一種韋伯氏的對目標的自我批判,與對實踐後果的不確定感。言下之意,這種拒絕入戲的姿態似乎是「僅存的反對態度」。
呂、錢二人的回應令人深思。在邊線模糊、眾聲喧嘩、價值無限紛亂、任何理想主義皆被懼怕與嘲諷的今日,作為一個左派、反對者、乃至一個人,我們該信什麼?該懷疑什麼?該堅持什麼理想?如果我們不信,那是不是連懷疑的能力都沒有?我們如何確定我們真的相信?如果,我們說我們相信,那是因為我們真實地經驗過(像經驗過麗日和風),還是因為我們的青春勇氣或知識邏輯?如果我們並不真信,是否還是不妨礙我們要別人信?我們真誠地反對(好比,威權、不義、不公),是否前提地要求我們真誠地相信(好比,解放、平等、民主)?人要作什麼樣的功課,世界要怎麼樣的改造,才能培養出堅韌隨和、脈脈如泉、自信且隨時對批評開放的世俗信念,從而讓我們從妒恨的反對、自傷的犬儒、與各種準宗教的庇護中超脫出來?這些大概都是問題。做左派於今很難,大約也是因為誠實地做人很難。這樣的一種布雷希特氏的質疑於今分外令人有所感。
在某種意義上,鄭鴻生的〈青春之歌〉就是一個布雷希特氏的史詩劇場,它不是要我們去認同劇中的人物與情節,而是要我們反省我們當下的存在。緣此,台社歡迎來自不同世代、不同立場的朋友提出回應。
這一期的《台社》主要是由兩個精悍專題構成,分別是「挑戰新自由主義」與「殖民統治與反抗」。對新自由主義的質疑是台社學術與政治的基調之一,我們繼上一期刊出了法國經濟系學生的宣言,這一期再轉載英國劍橋大學經濟系學生對新自由主義及新古典經濟學典範的批判宣言,並以此作為台社對此一議題的國際主義呼應。
專題一:「挑戰新自由主義」
從1999年《台社》33期的「解構東亞」專題起,台社開始了有關東亞區域批判論述的連結與互動,先後刊出了孫歌(33期)、趙惠淨(33期)、汪暉(37期)、與王謹(39期)等來自中國大陸與韓國的批判性論述,以及此間批判知識界的回應對話(37期)。我們進行這樣對話的企圖是跨出既存政治疆界,在區域尺度上進行批判知識份子的對話,分享觀點與經驗,跳脫偏狹的在地視角與族群中心主義,從而回過頭來再度培力壯大在地運動與思想。因此,這樣的對話其實本身就是運動的一部份。根據這個定位,本社將繼續進行此類對話。
作為本期「挑戰新自由主義」專題第一篇論文的〈“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及其批判〉就是這樣的對話的一個延續;作者汪暉是當代中國大陸的最重要的與最具爭議性的社會理論家之一。這篇論文是繼《台社》37期刊登了〈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之後,本刊第二度刊登汪暉的論文。這篇在華文世界首發的論文,由於對一些敏感的歷史與理論問題進行了先鋒且深入的探討,預期將受到區域內外批判知識份子的高度重視,引起的討論與爭議將不減於前一篇論文。
自七○年代中後期開始,以海耶克的「新古典經濟學」為核心理論形成的一套發展主義世界觀,一步步地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取得霸權,這個世界觀藉由攫取性個人主義的宣揚、自由市場的拜物教、民主的形式主義化、國家干預與規約的解除、福利國家傳統的淘空、以至於一切社會主義遺產的清除,挑戰了戰後西歐在資本主義黃金時期所形成的以福利國家為核心機構的集體安全制度。這個思潮與政治路線經常也被掛上「新自由主義」這個高度誤導性的前置詞,但事實上它和眾多具有爭取平等與民主的內在理路的自由主義傳統有重大矛盾(這一點汪暉在他的論文有精彩的討論)。到了八年代,新自由主義因為得到了英美兩政權的全力奉行而取得了重大勝利,隨後再加上八年代末前蘇聯與東歐國家的解體,更使得新自由主義思潮取得了空前的全球性霸權,「歷史的終結」與「全球化」一時也成為了新自由主義自我確認的核心語彙。但與此同時,全世界範圍內以及民族國家範圍內的社會平等以及社會正義情況急遽惡化、地球資源遭到更無限制的開發,而以新自由主義為意識型態的各種世界性經貿、金融或開發組織,也在全球的範圍裡遭受到激烈的抵抗。
雖然如此,新自由主義並非是一個統整的、同質的思想運動與政治計畫,它在各個不同區域有不同的生成背景、不同的主體構造、也有不同的社會效應,因此面對新自由主義的挑戰,各區域也有各自需要面對的特殊情境。汪暉這篇論文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勾勒出當今中國大陸的「新自由主義」是在什麼樣的歷史和社會條件下浮現的。
汪暉在《台社》37期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一文,是在思想的層次上,歷史地檢討了八年代與九年代初中國大陸的各種狀似殊途的左、右「啟蒙主義」與現代化意識型態之間的關連。雖然那篇論文並沒有直接處理新自由主義的問題,但其實已經指出了當代中國的各種思想潮流都缺乏將具體社會矛盾置放於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分析能力,從而主觀或客觀地成為了「當代中國資本主義的文化先聲」或「現代化意識型態的補充形式」。因為汪暉那篇論文的主要著力點其實還是在和各種思潮的批判性對話,因此雖然可說是基本上成功地指出眾多思潮的問題所在,但並沒有自我實踐出對各種具體社會力量的歷史分析。
在本期這篇論文中,為了要經驗地、歷史地理解中國九年代以來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無上正當化話語的新自由主義的源起,汪暉嘗試跳出思想史與意識型態批判的層次,將新自由主義擺在一個重要歷史事件——一九八九年的社會運動——的脈絡下研究。此地的流行識框幾無例外地把一九八九上半在中國發生的運動極度化約地定格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但在中國大陸,人們,知識份子尤然,似乎也一樣犯了對歷史的不當化約(從而是扭曲)的毛病,把一九八九年那個參與階層深廣、利益與訴求多元的社會運動,凍結在幾個歷史事件的表層上,無法對這個運動得以產生的歷史條件和基本訴求進行具解放性的回憶與理解。簡化與扭曲後的一九八九年社運因此被說成是「改革」與「反改革」兩造的對壘。對汪暉而言,這樣的一種扭曲性的化約就是新自由主義已然取得話語霸權的明證,因為它把基層民眾的素樸的社會主義傾向給消音了,也掩蓋了運動對改革過程本身的批判。
汪暉的努力目標就是要翻轉新自由主義的「反歷史詮釋」。透過對一九八九年社運的分析,汪暉指出這個運動的意識型態因素並不只是自由和狹義的民主,也包括了平等和公正觀念。要理解一九八九年社運,不能不理解一九八五到八九年之間中國大陸經改的現實效應。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透過權錢交換與放權讓利,中國大陸出現了嚴重的社會不平等與新的等級制度。基本性格屬於城市運動的一九八九年社運就是以學生、知識份子、工人、和其他市民階層為動員基礎的對「舊時代的告別,也是對新時代的內在的社會矛盾的抗議」。這個內容複雜,也不乏矛盾訴求的運動被新自由主義描繪為僅僅是追求「自由」。但問題一直是,誰的自由?
汪暉認為中國大陸一九八九年的社運和一九九九年西雅圖、二○○○年華盛頓的反WTO的抗議,有深刻的內在聯繫,都是反抗新自由主義的運動,因為它們都把「民主、自由的價值與社會保護運動密切聯繫起來」。在這個意義上,汪暉重申理解中國現狀無法使用傳統/現代,東方/西方的二分語言,必須把在中國所發生之事置放在反思現代性的全球視野內。唯有透過對於現代性的歷史批評,我們才能具體地在知識上呈現出展開中的社會矛盾。對汪暉而言,這是檢驗社會思想與實踐關係的有效判準。因此,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不能僅僅是道德層次上的批判,而必須要在它的話語和實際的社會過程中建立歷史的聯繫,指出表述和實踐之間的差異。這個現代性的觀點也必然是全球的觀點,能夠避免掉入國族中心主義的盲點。
新自由主義在今天中國大陸的展現具有複雜的面貌,是涵化激進市場主義、新保守主義、和新權威主義等多種意識型態的變形蟲:「在穩定條件下要求放權讓利的過程激進化、在動盪的條件下以權威保護市場過程、在全球化浪潮中要求國家全面退出。」正因為這樣,它的質疑者與反抗者也不是一個同質單一的思潮或運動,而是包括了多方面,有來自自由主義本身的各種理路、有來自對資本主義的歷史分析、有來自那些希望重新發掘社會主義進步傳統的努力、有來自反抗帝國主義霸權的思潮、有來自對亞洲的重新思考、有來自對中國革命的重新評估、有來自女性主義、生態保護……等種種不同的關心與出發點。這些一九九七年左右開始萌芽的各種解放性思潮都可說是在以各自的方式面對一九八九社運所從出的社會條件,只是如今這些激發那個運動的條件更加惡化罷了,其中特別突出的無過乎那些來自農村、佔全中國總人口十分之一的內部流勞的次等國民的惡劣處境。
為什麼要反思新自由主義?汪暉的規範性目標定在為三個目標(民主的市場、社會的自我管理、和民間力量的培育)提供理論基礎。因此反思新自由主義為的就是要拉出一個民主計畫。在這個計畫中,汪暉再度呼籲知識份子(儘管當今的知識份子面臨了二十年專業化所帶來的脫離社會現實的危機)的民主介入,而知識份子所能做的就是在理論層次上談出社會運動與制度改革兩者之關係的道理,把從工人、婦女、農民、一般市民立場發出的社會保護運動和現實上的制度改革掛上鉤。沒有這一層功夫,那麼就不但無法為社會整合找出真正的民主道路,反而還會錯怪受害者——像余英時那樣的知識份子把一九八九年的社會運動籠統地定位為激進主義的表現,把中國近百餘年來所有問題的解決歸結到「汝不可過激」的箴言戒律上。
汪暉的這篇論文是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一個理論與政治介入的里程碑,應該和他前一篇探討現代性問題的論文合而觀之。這篇論文對社會運動(以及更廣泛層次上——社會性)的解放潛力的認真而不浪漫的正面評估態度、對民主經濟與民主社會的規範性肯定、對現代性解放潛力在出發點上的肯定、對現代國家在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的角色期待,都一定程度上間接地回應了台社幾位同仁先前對他前一篇論文的評論與質疑。我們期待在這篇論文之後,有更多的研究,能夠在這篇論文的基礎上,更深入更細緻更歷史地追索這個中國特色的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範圍的新自由主義是如何接軌?產生什麼樣的交互影響?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的論述是透過什麼樣的社會與文化機制獲得霸權位置與進行再生產的工作(汪暉問道:「普通民眾、甚至知識份子對〔WTO〕這一協議的內容一無所知,為什麼他們如此興高采烈?」)?一九八九年的社會運動的雙重或多重性格是如何形成的?(是否可期待一種類似《霧月十八》的具體社會力量的歷史分析?)為什麼自由民主和平等反剝削的聲音沒有被串起來,有沒有思想層面以外的原因?參與者的多重聲音(例如「社會保護」)是否能更具主體性地再現?
我們對汪暉的這種立足於特定文化與政治空間進行論述實踐,但同時又不忘將之置於一世界史的視野表達敬意,對論文中那種坦率與各種思潮論述交鋒的態度也表欽佩。希望這篇論文帶給本地批判知識界的不是另一篇有關中國現狀的研究,而是從這樣的研究中反照存在於我們社會中的新自由主義霸權以及反思我們對應此一霸權的方式與路徑。把這篇關於當代中國大陸思想狀況的論文以「這個故事說的就是你!」的敏感來閱讀,才是全球與區域公共空間存在的意義。
新自由主義及其經濟學學理核心——新古典經濟學——在中國大陸駸駸然形成關於社會、政治、與市場之間關係該如何架構的主導性意識型態。在中國大陸,新自由主義是藉由各種現代化的意識型態,以傳統與現代的二分隱喻為敘事手段,把市場自由設定為現代性的唯一標竿與目的,從而在瓦解「傳統社會」及其素質之時,進行激進的放權讓利,合法化權錢交換,造成了社會的嚴重不平等與新等級制。在台灣,這個意識型態則似乎也是大約在同時也取得了它的社會與政治正當性(當然在學院裡,新古典經濟學似乎早就一直是受美國主流經濟學訓練的經濟學教授們的皈依),而這個正當性的取得,其實和對岸有異曲同工之妙。台灣的「新古典經濟學」教授們也是藉由某種傳統和現代的強勢隱喻,來推動市場自由以及所謂的「民營化」;黨國其舊,市場維新——表現在《解構黨國資本主義》這本書的出版所象徵的運動上。瞿宛文,這位台灣經濟學界屈指可數的(甚或僅存的?)異聲,就曾在《台社》20期對這個運動提出批判,指出這個運動以反抗威權的批判性為姿態,但轉過身來卻是毫無批判性地支持全面自由化,解除市場的所有政策限制。瞿宛文在那篇論文的結尾這樣說:「在當今黨國威權體制解體重組之際,反抗威權不能再是我們唯一甚或主要的任務,當今亟需的是更複雜化的公共政策討論。」
的確,新自由主義者所反對的正是「複雜化的公共政策討論」,因為他們經常抱持著類似神學家的信念:只要國家放手不干預市場,市場一定會自發地形成某種秩序,並趨利避險。對於作為一種重要公共政策的產業政策,新自由主義者不是認為一定有害,要不然就是至多無害(也就是多餘),而支撐的論述則多是「理論」層次上的必然性宣稱。瞿宛文在這一期的論文明確指出,這樣空洞的純理論爭議是無意義的,重點應該在「瞭解成功的條件與失敗的原因」。
是在這樣一個質疑新自由主義教條化與神學化的知識基礎上,瞿宛文的〈台灣產業政策成效之初步評估〉詳查了台灣七年代以來的五種重要產業的成功與失敗的案例,指出雖然產業特性本身對一個產業政策的成敗是有影響,但產業政策的制訂、執行及其品質還是具有重大影響力的。一個鮮明的例子足以說明國家的政策與執行的重要。台灣的積體電路的發展現在已經成為台灣產業的科技與獲利前鋒,但這個產業的興起並不是靠是自由市場的自發性或是企業家的創發性,而是經由國家在七○年代中期成立的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子工業研究所,向RCA購買技術,成立試驗工廠,在技術成功後,再將工廠移出,成立私營的衍生公司——聯華電子,以及之後的台積電。
由於風險社會化的緣故,公營企業擔綱的發展路徑有效地降低了新興產業發展初期的私人投資風險。瞿宛文提出風險社會化作為肯定公營企業(以及更廣泛而言,作為公共政策的產業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時,瞿宛文也簡短地比較台灣和南韓在國家角色上的差異。她指出,相較於台灣公營企業的風險社會化作用,南韓的作法則是政府承擔主要風險,因為政府是透過支持少數私人財閥來擔綱。南韓模式的優點是「擔綱者沒有公營企業的包袱,壞處則是其明顯對分配方面比較不利。」因此,瞿宛文的論文雖然只是集中於探討為何某些產業會(商業上)成功,而某些失敗,但這樣的討論邏輯上也應該會拉出關於產業政策對於社會分配、社會正義上的討論。我們因此可以追問:台灣的國家機器在扶植新興產業上除了將風險社會化之外,是否也帶來了「效益社會化」的好處呢?後者是否也該更系統地納入台灣產業政策「成效」的評估之中呢?當然這種社會成效的考評牽涉很廣,並非易事,但我們也堅決反對現在流行的「民營化」說法,一面倒地宣傳市場神威,醜化國營企業。(這些污名化的語言,例如科層制的僵化、效率不彰、政策綁死、訊息不足……在瞿宛文的這篇論文中均遭到程度不等的駁斥。)我們還要指出,歷史地看,台灣的國營事業曾是廣大台灣勞工的薪資與勞動條件的參照高標,這個相對進步標準若遭廢棄,整體勞動條件的下滑也是預料中的事。
專題二:「殖民統治與反抗」
姚人多的〈認識台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台之殖民治理性〉是這個專題的頭一篇論文。在這一篇論文裡,姚人多以一種傅科式的實證主義對薩伊德的東方主義以及更廣泛的後殖民文化研究提出批判。姚人多認為當今流行於學界的後殖民研究,過份著迷於殖民帝國如何二元論地透過對殖民地人民的「扭曲」,建構出自我表揚的種族神話。在這樣一個大致對焦在以文學文本為基礎的文化想像的研究路徑中,似乎一談到殖民知識,就「立刻搬出再現、想像、扭曲、模糊、混雜、模仿等概念,彷彿再現與現實之間永遠有一條鴻溝,彷彿殖民權力永遠是一個不喜歡事實、不喜歡真理的權力,彷彿殖民國家什麼都不會只會一昧地醜化被殖民者。」
相對於這些強調想像是殖民統治術核心的研究進路,姚人多強調的核心則是各種調查與普查這類傅科所謂的理性知識。透過這些繁瑣的對人口、地理、人文、自然的明查暗訪、逼供、與自白,統治者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被現實地、經驗地落實在日常生活之中;統治者新來乍到時所有的各種不確定感一掃而空。在殖民者的眼光中,殖民地人民是草木蟲蠡,都可以透過細密的科學調查得到確切的掌握。知識因此是力量,目的是「製造馴服又有用的身體」以為統治與剝削(後者惜乎未多作討論)的基礎。這些真實的資料不是幻覺不是錯覺也不是想像,它們理應是治理的依據。作者以一種傅科的口吻指出,殖民知識「的作者不是什麼文學大師,而是派出所的尋常警員。」
姚人多的總問題意識是殖民統治的治理性是建築在什麼基礎上,它如何可能?次一級的提問則是日本對台殖民統治在全世界範圍內的殖民歷史中有何特殊性。強調統治術的微觀物質基礎或許會招來常識之譏,但這個研究的特殊意義或許正是要以明白顯然之理來挑戰後殖民研究典範的那種以民粹為名的知識菁英氣。從政治社會學的觀點,這個研究的意義在於指出權力的微觀物質與生命基礎,對傳統政治社會學的壓抑權力觀提出了質疑——作者指出被殖民者其實並非是在大權力五雷轟頂下敢怒不敢言的沈默者,而是在一種被強迫發言的權力部署下「對權力訴說很多故事」的人。
儘管作者質疑這個「強迫人發言的權力可能比壓抑人聲音的權力更陰險、更狡猾、更難反抗」,讀者或許還是會質疑在這個研究中,被殖民者的主體性到底跑到哪兒去了?這的確是個問題。也許我們沒有理由期望這一篇論文也能兼顧這個問題,但我們期望將來能夠看到有關治理性與被殖民者主體性之間的辯證的、歷史的關係的研究的出現。雖然如此,這篇論文在反抗(殖民)統治這一問題上,仍是有被挪用的可能的。我這個挪用和本篇論文接榫的地方即是,如前所述,對某些所謂的後殖民研究的批判立場。如果說,統治權力不只是來自不懷好心地、絮叨地敘述認同的故事,而也在對「理性知識」的掌握,那麼反抗之道恐怕也少不了同樣以「理性知識」為手段對殖民者的「理性知識」的內在矛盾的揭穿,以及對那些為反抗力量所需要的「理性知識」(通常是結構的與歷史的知識)的探知。這個傅科晚年的理論與政治的aporia,需要我們嚴肅的面對。
「被殖民者的主體性到底跑到哪兒去了?」這個問題則是方孝謙最近的研究所要處理的問題之一。方孝謙的研究也現身說法地指出(後)殖民研究並不一定要一直緊跟著東方主義的問題意識後頭。在《台社》37期的〈英雄與土匪:日本據台初期的敘事認同〉一文裡,方孝謙藉西來庵抗日事變指出殖民統治者與反抗者各自在經營敵對性的敘事認同策略,統治者伊能加矩以一種現代的、高等的文明姿態給抗日者貼上「本島人土匪」的標籤,並將後者文化地定位為「好利、迷信、與情浮意動」。西來庵的會眾則從傳統文化中汲取資源,透過貌似迷信的善書與儀式,找到自身認同的殘餘文化支撐(例如篤信因果、敬神孝親、嚴防財色……等),從而得以不從日本殖民統治者的眼光凝視自身,並得以藉由區別他我,證成抗爭主體。
在這一期,方孝謙繼續這個主要關懷,把研究對象擺在日據後期的小說(家),透過他們與他們的創作,耙梳出彼時本島人的認同光譜。原來,本島人的認同並非鐵板一塊,而是有一個階級的斷層,下階層的漢人因為生活世界中所立即感受得到的剝削與壓迫,很容易把「我(們)」和他們(地主、資本家、殖民酷吏)對立起來,相對來說,那時候受日本教育的知青則是經過一些轉折,漸次地認同於日本人。同情庶民,但方孝謙並沒有譴責知青,他深入地、移情地理解這些知青在嘗試各種認同與歸化策略之後還不免「理解到不論我如何做,我還是『次日本人』」。不管是庶民還是知青,他們要在劇烈世變之下仍能維持自我的一個方寸之地,那還是只能回過頭來依賴傳統文化(例如傳統禮儀家法與漢文教育)。方孝謙用Raymond Williams殘餘文化的概念指出傳統文化並非糟粕而已,在弱者的抗爭與自我認同的維繫上,扮演了反抗霸權的重要角色。方孝謙的這個論點某種程度上超越了黨派意氣之爭,能夠為被污名的弱勢者(不管是庶民還是知青)翻身正名,也看到他們的「弱者的武器」。就這點而言,這是從E.P. Thompson以降英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史,與從RaymondWilliams以降的古典文化研究的一道閃爍傳統。我們樂見到類似的研究能夠繼續在本地茁壯。
方孝謙在論文尾聲的論點似乎較易引起爭議。他把上述傳統文化之為用的論點拉高到現代性與傳統的關係上談,指出「現代性自我」是藉斷絕傳統的道德秩序而成立的,從而以聽起來有些傳統主義的方式作結論:「沒有傳統秩序做集體記憶基礎的人,在認同摸索的過程中找不到暫時可以安錨立足的地方」。雖然這個重要宣稱惜乎未在理論層次上進一步發展,但已經碰觸到了理解現代性這個核心的社會與文化理論問題。在我們思考反抗的問題時,我們沒法不深入思考在當代情境下,反抗的基礎、力量與資源要到哪裡尋找?
專題一:「挑戰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及批判/汪暉(42 民 90.6 頁 1-66)
本文是對1989年社會運動與當代中國大陸的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歷史根源的分析,文章共分三個部分。文章的第一部分是對1989年社會運動的歷史分析。與許多有關1989年學生運動的流行解釋不同,作者將這一運動視為一場成分複雜的社會運動,並通過1978至1989年年中國改革過程及其內在矛盾的研究,仔細地分析了這一運動的複雜的構成、不同社會群體的不同的訴求,以及運動得以發生的社會條件。文章的第二部分在後一九八九的歷史語境中討論中國大陸知識界的思想狀況,分析了知識界對於一九八九社會運動的反歷史的總結方式及其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聯繫,並圍繞市場化、私有化、全球化、民族主義、亞洲等問題,剖析知識界的理論分歧和思想分化。最後一個部分簡要說明了作者反思現代性問題的幾個主要面向。
關鍵字:新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放權讓利、社會保護運動、現代性
This paper is a study of the 1989 social movement and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neoliberalism in China.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is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1989 social movement. Differing from mainstream interpretations on the student's movement in 1989,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movement was a social movement which is composed of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in urban areas and explains why those groups, who had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backgrounds, got involved into the movement.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aper is an analysis about intellectual discussions and debates against the post-1989 context. Focusing on issues such as marketization, privatization, globalization, nationalism and Asia, the author gives us a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 liberal trend and its critique. The last part i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meaning of rethinking modernity in Chinese context.
Keywords:neoliberalism, neo-authoritarianism, informal privatization of the state, movement for protecting society, modernity
台灣產業政策成效之初步評估/瞿宛文(42 民 90.6 頁 67-118)
本研究比較台灣五個產業(石化、鋼鐵、積體電路、汽車、造船)的發展過程,著重點在於評估產業政策在這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檢驗新古典以及修正學派的相關理論。而結果發現:1)一個經濟體在當時的各種條件雖會限制其所可能發展產業的範疇,限制產業政策所能選擇的範圍,2)但是這限定出來的範圍相當廣泛,以致於產業政策的協調作用、社會化投資風險、以及幫助決定發展策略的功能,有相當大的發揮空間;3)但這只是潛在的可能性而已,產業政策的設計以及執行必須合宜,這些潛在的功能才有可能實現,而這確實是不容易做到的組合,同時,4)各個產業的特性,配合上政策環境的各種主客觀條件,就可能會使得各個產業的產業政策的設計與執行上的適切性有所差異,因此進而導致這些產業在經濟表現上呈現差異。
關鍵字:產業政策、產業研究、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成長因素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five of Taiwan's industries, which have been targeted for promotion by the government. The sectors studied include petrochemicals, steel, integrated circuit, automobiles, and shipbuilding. The study compares differences in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conditions, and the policy measures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in each sector, and weighs them agains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ector's performance, so as to discern the elements which are necessary of sufficient for the policy to be effective. It is found that 1)though various conditions limit the range of options or potential targets(industries)available to the government, the limiting effects are far from determinant; 2)and leave a lot of room for industrial policy to play a role; 3)however, only if policies are appropriately designed, schemes effectively enforced and policy measure properly carried out, then industrial policy could have its desired effects; 4)differences in the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and in policy effectiveness were found to be responsible for differences in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these five industries studied.
Keywords:industrial policy, industry studies, East Asian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causes of growth
專題二:殖民統治與反抗
認識台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台之殖民治理性/姚人多(42 民 90.6 頁 119-182)
被殖民者到底有沒有被正確地再現到殖民者所建構的殖民知識與殖民論述中?自薩伊德的《東方主義》以來,所有有關殖民主義的議題都或多或少圍繞著這個問題在打轉。這篇關於日據時期台灣殖民知識的論文也不例外。我們將從以下這個簡單的問題開始:到底什麼是殖民知識?難道只是竭盡所能地把被殖民者扭曲、建構成「他者」的扭曲,好來滿足殖民者優越的自我形象?我們所提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事實上,我們認為這種說法基本上是起源於對殖民權力本質上的誤判。接下來,我們將把討論的焦點移到日據時代的土地調查及人口普查,我們將從傅科「治理性」的角度來看殖民時期的知識。此處的談法並不著重於歷史的紀錄,而在於點出這兩種調查所呈現出來的知識類型,及其背後所代表的政治理性。在殖民者所繪的地圖上,我們找到了規訓權力那種對知識的精確性、詳細性的要求,而在人口普查中,除了這種精確性與詳細性之外,我們還看到了一種把整個被殖民者當成一個「人口」的生命政治理性。無疑地,本文是傅科許多觀念上的應用及延伸,我們運用傅科的目的不只在於解釋台灣過去所發生的事,更重要地,還在於與西方既存的殖民理論對話,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本文中我們不斷提及歐洲殖民主義的原因。
關鍵字:殖民主義、殖民知識、規訓權力、治理性、地圖、人口普查、統計、數字、傅科、生物政治、薩伊德、東方主義、再現
Had the colonized been correctly represented in the colonial knowledge and discourse? Since Said's Orientalism, all the issues concerning colonialism have more or less revolved around this question. This paper, arguing the colonial knowledge in Taiwan, is no exception. We will begin with a simple question: what is colonial knowledge? Is it nothing more than construction of the colonized as an Other? Is it a systematic distortion of what the colonized really is? The answers we want to offer are negative. In fact, we believe, these kinds of argument are derived from a misjudgment of the nature of colonial power. In this paper, we will bring the land survey and census both launched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to spotlight. Far from being a detailed history of these two surveys, what we are going to do here is mainly to find out the form of power and the political rationality behind them. In other words, there surveys will be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ucault's idea on governmentality. In the maps produced in the process of land survey, we witnessed the accuracy and all-embracing nature of the colonial disciplinary)knowledge; in the census, apart form the accuracy and detail-ness, we witnessed that the Japanese colonizer actually treated the Taiwanese as a population, which is indeed a sign of bio-political governmentality. In many respects,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apply Foucault's theories to Taiwan. Not only do we want to explain what happened in colonial Taiwan differently, but we want to have some conversations with contemporary post-colonial theories. And this is exactly the reason why in this paper we constantly refer to the European colonialisms.
Keywords:colonialism, colonial knowledge, disciplinary power, governmentality, map, census, statistics, number, Foucault, biology politics, Said, Orientalism, representation.
日據後期本島人的兩極認同/方孝謙(42 民 90.6 頁 183-228)
運用Hayden White喻格理論中「主要指涉」(敘事論述向外指向客觀世界)與「次要指涉」(敘事論述向內指向語言而賦予作者與讀者共享的感情與態度),我們分析日據後期(1931-1945)兩類台灣人小說:庶民與知青文本。在庶民小說方面,分析結果認為即使在積極同化台灣人的所謂「皇民化運動」之下,工農婦女仍是以仇日及仇視一切剝削者,並藉助鄉土固有文化資源做為認同的基礎。而在當時的知青小說方面,則顯示第二代受日式教育的台灣青年在既受排斥又不得不接受的情況下,沿著從「理性算計」到「神秘順從」的態度光譜,逐漸認同於日本人的「皇民意識」。知青的認同轉變,我們並佐以真人實事的葉盛吉的「雙鄉」認同來做對照。透過日據後期的庶民與知識青年呈現兩極認同的分析,本文旨在說明:「我是誰」的困惑要得到抒解(儘管通常只是暫時的開脫),固有的文化資源是不可或缺的支柱。
關鍵字:喻格、主要指涉、次要指涉、認同、殘餘文化
To analyze the sense of identity implied in Taiwanese short stories and novels written in the 1930s and the early 40s, we appeal to historian Hayden White's notion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referent." While the former means the reference of a discourse to the outer objective world, the latter means that to the inner emotions and attitudes shared by both narrator and his or her audience. By using the two notions, we conclude that, in the short stories concerning the masses, their identity appeared to be based on the resentment of the "others," meaning both colonial and capitalist exploiters who took advantage of labor and female bodies of the masses. In the stories concerning Taiwanese intelligentsia generated from the Japanese educational system, the elites revealed their differential degrees of identification with Japanese culture, ranging from an attitude of rational calculation to that of mysterious submission. Finally, we suggest that what Raymond Williams called the "residual culture" is necessary for buttressing one's sense of identity in a situation such as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Keywords:identity, primary referent, residual culture, secondary referent, trope
議題與回應
「不堪回首」之下的回首/呂正惠(42 民 90.6 頁 229-240)
今下天午三點左右,我拿起鴻生《青春之歌》的打字稿本開始閱讀,不到十頁,我已完全沉迷於其中。吃過晚飯,略事小寐以後,立即接續下去。這樣,一直到了凌晨一點,終於讀完。掐指一算,至少用了八個半小時的時間。經過這麼長的全神貫注的閱讀,雖然頗有倦意,但正在全速開動的腦筋卻不肯休息。於是決定開筆寫這篇回應。我所以有幸受邀來寫回應,原因不難索解。第一,一九六七年(民國五十六年)我進入台大中文系就讀,比鴻生高兩屆,完全是同一世代的人,成長的心路歷程非常相似。第二,我在大學時代就已認識本書主角之一的老錢(永祥),雖然交情不深,但總算認識。第三,我「看過」台大哲學系事件的一幕,勉強可以算得上目賭者。第四,本書的另一主角王曉波,以及本書常提到的陳映真現在跟我都是「中國統一聯盟」的盟員,他們都是我的「先進」,我或者可以對本書敘述的七○年代初期出現於台大哲學系的右翼民族主義發表一點感想。
青春歌聲裡的低調/錢永祥(42 民 90.6 頁 241-)
鄭鴻生兄將我們少年時代共同渡過的一段經歷寫成了文字,並且邀請我攀附書後,發表一些感想。本書的內容雖然屬於嚴肅的歷史—實踐反思,不過書中難免涉及那些慘綠歲月的一些舊事、私事,其中不堪回首者居多。而佔用公共場所曝曬「嬰兒時代的鞋子」(或者其他本應屬於私人、私室的事務),更令我覺得失措而尷尬。可是鴻生容許我在他的故事之後續貂,於我乃是三十幾年共迎風雨、相濡以沫所換來的莫大榮幸,我不能不鄭重其事。鄭重之道,莫過於不要打擾他敘事的思路蜿蜒和情緒起伏,而是設法自行提供一個「入戲觀眾」的若干思考,說說我在年過半百之後,是如何理解、感嘆那段經歷的。
其實,三十幾年以來,我對於自己成長的那些年頭、那些人與事,不敢回首之外始終也有難捨的眷戀——那是一群活得認真的朋友、一個自信不平凡的時代、一段豐富而狼狽的經歷。眷戀之餘,自然也思索過其間的「意義」,尤其是超乎個人而較為客觀層面的意義。這樣做,勢必需要將個人的經歷聯繫到歷史、聯繫到自己當時身處的時代與社會脈絡。可是每每我會發現,自己的回憶與今天台灣社會所提供的歷史記憶有些枘鑿。無庸諱言,我們一批老朋友,與當前台灣的主流意識形態是有相當距離的。不過我本以為,與自己社會的「主流民意」維持一段距離,乃是知識份子的本分,並不足以為奇。可是一旦距離居然造成了極為不同的歷史回憶,便構成了一個有著相當反思餘地與個人興趣的問題,值得作為反省的出發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