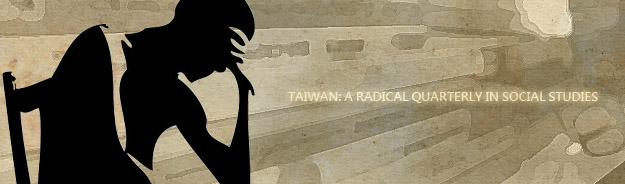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43期:
編輯室報告
省籍問題及其相關的族群與國族主義議題一直是《台社》的關切:1994年《台社》17期〈帝國之眼:「次」帝國與國族——國家的文化想像〉一文引來後續六篇回應,1995年《台社》19期〈認同政治的待罪羔羊:父權體制及論述下的眷村女性〉直接處理省籍、階級、性別與族群民族主義問題,之後,我們陸續出版了1996年21期的「國族主義」專題,1997年28期「國族與殖民主義」專號,以及2000年40期「台灣論‧論台灣」專輯。總體而言,這樣頻繁的討論族群及民族主義相關問題,其實是反映了這些環環相扣的問題是台灣社會的真實矛盾,其中省籍問題又是核心的問題。
省籍問題跟很多其他第三世界社會戰後的族群衝突一樣有其特定的歷史基礎,它主要的表現形式和政治動員/召喚息息相關,隨權力集團內部權力的消長產生變化,而台灣的複雜性則在於它又與統獨問題交叉重疊。從戰後國民黨政權來台至今,經過了數次的轉折,隨著政權的更替,省籍問題的內容與形式及其觸動的情緒強度也一直在變,感覺結構也一直在轉化;台灣社會中國家機器所投射出的龐大象徵權力是不停地波及到民間的日常生活的。我們可以找出其中的幾個關鍵轉折點:228及其後來被建構成的象徵意義;蔣經國統治後期所謂吹台青的本土化政策;李登輝上台後與郝柏村的鬥爭,及郝失敗後,代表舊國民黨勢力的新黨出走;94年的省市長直選;96年第一次總統直選;以及
2000年總統選舉,代表本土反對勢力陳水扁的上台。在一個切面上來看,這些具有標竿意義的事件,其實意味著省籍問題逐漸從暗流走向前台,兩蔣的高壓統治下黨外反對陣營中是以自由民主為表面語言,但省籍動員則是實際運作的暗流,也多元決定了民進黨成為所謂「本省黨」的基本性質;相對民進黨而言,新黨也就成為所謂外省人的代言人。是在這個族群政黨政治的大架構下,出現了民新兩黨喝咖啡大和解的劇碼。不過大和解顯然是政治姿態的成分居多,省籍問題依然持續地在運轉。隨著陳水扁執政,民進黨卻無法掌握立法院多數決議權,於是有所謂扁李合,對抗連宋合的講法,其中,省籍問題還是重要的軸線。
因此,省籍問題一直是政治角力的核心場域之一,它一直牽動整個社會的神經,然而卻是知識上公開討論的禁忌。想要批判性地去分析解釋省籍問題一直是相當困難的:任何的分析都會快速地與分析者的省籍身分劃上等號,這暗示著身分認同政治在台灣社會,特別是在批判知識圈,的高度支配性。作為左翼學術團體,《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對於省籍問題一直抱持著批判的態度,但同時我們也認為省籍問題是不能迴避的主流社會的政治動員力量,我們認為要透過對它的運作機制的剖析,才可能介入這個社會、政治過程,也才可能消解政治人物的動員。同時,要指出的是,我們不願意附和政治人物所謂大和解的口號,更不認為大和解是簡單的問題,唯有從冷靜的思考出發,才可以開始突破省籍問題的禁忌,從反思性的討論中尋求省籍問題的出路。
本期〈大和解?〉專號集結了文化研究學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與其他團體在2001年五月二十六日共同主辦的「為什麼大和解不/可能?——省籍問題中的災難與希望」第四場文化批判論壇中所發表的兩篇論文:廖朝陽的〈災難與希望:從〈古都〉與《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看政治〉及 陳光興的〈為什麼大和解不/可能?〈多桑〉與〈香蕉天堂〉殖民/冷戰效應下省籍問題的情緒結構〉,與朱天心、宋澤萊、邱貴芬、鄭鴻生的四篇回應,以及陳映真針對其中一篇論文的評論。這兩篇論文的重要性在於將焦點擺在歷史——結構性的情緒、情感層次,討論殖民主義與冷戰的雙重結構造成了什麼樣的台灣獨特歷史經驗與認知斷裂?此結構下的省籍差異引發了什麼樣的情緒性感情結構以及主體的欲望?台灣的文化象徵形式如何面對統獨爭議、認同危機、文化分裂與政治鬥爭等問題?災難論述之中,我們是否可以窺見新希望的可能性?它又向我們展現了什麼樣的契機?朱天心、宋澤萊、鄭鴻生的回應都以個人親身經驗及感情出發,豐富化也複雜化了兩篇論文的討論,反思性地指出省籍矛盾中的真實歷史經驗問題。邱貴芬從庶民文化及歷史記憶的觀點對兩篇文章提出批評。陳映真則從台灣史內部的事件指出陳光興論文分析上的不足。
這一組文字,我們認為是檢討台灣省籍問題的重要歷史文獻。共同的、坦白的面對真實的歷史記憶/經驗,企圖解釋省籍問題的和解為何是困難的?所謂和解到底又在哪些層次操作?面對這些問題,這些述說是從具體的經驗為起點,而不是以理論語言來閃躲真實狀態。這樣企圖跨越認同政治的公開討論在台灣知識圈是第一次,也是對禁忌的破解。從作者們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政治人物急於大和解是在處理立即的政治僵局,而所謂的和解其實牽扯到相當多的操作與分析層次,從家庭內部、社會階級、族群分化、兩岸關係、亞洲區域,乃至於全球性的冷戰效應,環環相連;喝咖啡的簡單政治姿態並不能掙脫長期的歷史記憶及政治建構。因此,和解其實是龐大的歷史工程,是要長期地在所有日常生活的層次裡反思性地面對。總體而言,兩篇論文與五篇回應是在開啟討論問題的空間,提出多重層次的問題,也證明了省籍問題的坦白對話是可能的。我們將這組討論定位為提出問題的起點,我們期待讀者的回應,也希望逐漸深化台灣省籍問題的討論。
本期的一般論文有兩篇,分別是夏曉鵑的〈「外籍新娘」現象的媒體建構〉以及林文玲的〈米酒加鹽巴:原住民影片的再現政治〉。在一個很根本的意義上,這兩篇論文其實是「大和解?」專題的延伸——台灣社會難道沒有主流群體和原住民、「外勞」或是「外籍新娘」大和解的問題嗎?這個和解難道不牽涉到各種複雜的現代性問題(例如大眾媒體、民族國家、階級社會、多元文化主義、科層化組織、學院知識生產、「第三世界」……)嗎?
如果把省籍關係擺在「台灣人」和原住民、「外勞」或「外籍新娘」的關係的背景下來看,也許省籍之間早就大和解了,因為在一致地把,好比,「外籍新娘」當作「社會問題」的時候,本省人和外省人都立刻成為了相對於「他們」的「我們」。夏曉鵑繼續她在《台社》39期發表的關於資本主義下的跨國婚姻的論文,在這一期的《台社》接著探討台灣社會的媒體(與知識界)是如何地把「外籍新娘」和她們的台灣先生(通常來自下階級),建構成社會病理性的他者。這篇論文揭穿了台灣的新聞媒體是如何的不學有術,如何借用措辭、抄襲、道聽途說、想當然耳、與捏造數字等法寶,打造與繁衍一套有賣點的歧視說法(也許可以深入探討這種歧視罐頭為什麼銷路特好!)。針對媒體的這種對於情境定義的非常不對等的優勢力量,夏曉鵑呼籲知識份子應該摒除虛無的相對主義與孿生的不行動主義,傾聽弱勢者不連貫甚至不成句的話語,將她們的話語「重新政治化」。在現代法海與白蛇的鬥爭中,你要站在哪一邊?還是不站邊?——似是這篇論文所要質問於讀者的。
和解的前提是相互主體性的理解,但要達到這樣的理解則要透過鬥爭——似是這篇論文未言明的警語。
林文玲的論文藉由對兩部探討原住民身份認同政治的「原住民影片」的閱讀,指出兩種原住民運動的原型:一種是回到部落回到祖靈(由部落小米酒儀式保證),切斷主流社會所提供的認識框架、價值導引與污名認同,尋求建立個人進而部落的自信與自治。另一種則是接受主流社會四大族群的分類,參與到多元文化的政治舞台。後者這個似乎是已成定局的路線實則又充滿了進退兩難的焦慮——既要融入大社會中,又要追求/展示自己的特殊的、真實的味道(鹽巴之味)。如何在都會中展演部落?如何以現代知識展現部落純質?要找回自己還是讓他人看到自己?因此成為了揮之不去的大問題。從某一個角度解讀這篇論文,我們其實可以說它是在討論「多元文化」這個高度政治正確載重的名詞的真正意義。從政治權力的角度來說,如果原住民部落沒有真正的(即,有文化自信的)自治權力,那麼菁英代表制在多元文化國家中的意義不就是去多存一嗎?從文化主體性的角度來說,如果原住民部落沒有因找到自己的味道(鹽巴)而壯大,那麼壯大的不就只是「多元文化國家」這個現代形式嗎?一個根本的問題或許是,用本期專題的話語,弱勢群體(例如原住民)要先和多元文化的現代國家大和解還是要先和自己大和解?
「大和解?」專題
災難與希望:從〈古都〉與《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看政治/廖朝陽(43 民 90.9 頁 1-40)
班雅民認為「後延性」是一種分開現實存在與轉化提升兩個層次的歷史力量。這兩個層次的分離同時也帶出一個烏托邦面向,透過時間的顛倒來辨認過去記憶中所含的,未來的希望。安德生延續班雅民的想法,認為民族國家的產生是以後延性消失,成立「性質統一,內容空白」的時間觀為前提(這樣國家才不會因為過去的魅影不斷入侵現在而向其他時間轉化)。本文希望重新檢討這個問題,並透過時間異態的掌握來推演趙剛提出來的「民主民族」主張,指出民主民族如何在過去與現在、普世性與獨特性之間找到平衡點。
在二十世紀末,台灣出現了兩個小說作品,總結了近數十年來的台灣經驗,描寫現代性走向倒錯病理所造成的災難,並且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展演了班雅民現在與過去互參的歷史觀。朱天心的中篇小說〈古都〉用寧靜悠閒的京都來對襯陷入失憶狀態,不適人居的台北,透過個人的回憶與歷史反覆的規律來建立否定現狀的欲望。在這裡,對過去的執戀表達出參與現在的要求。重演過去意思不是要得到一個堅固不變的基點,而是要建立過去與現在相互更新的可能。宋澤萊的長篇《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則結合在地法術與歐洲魔鬼傳說,為社會腐敗、政治失序的災難尋找出路。故事裡的撒旦雖然永遠存在,但是災難既然總是以新事件的形式,在現在發生,其中其實也暗示了拯救的希望也是一種過去參與現在的翻轉動作。這兩個作品似乎都肯定經驗跳接的價值,認為過去切入現在可以為面對危機,走向滅亡的共群帶來新的識見。
本文認為,我們可以從上述文學作品的表現觀察文化認同的定位,也可以進一步從新民族轉變、形成的大框架來觀察相關問題。這樣的觀察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民主民族的根本意義可以怎樣開展。回歸「傳統」在這裡當然不可能是將一個開放的過去變成有內容,對現在施力的「固定標簽」。另一方面,布洛赫早就告訴我們,一味否定人含納於特殊性、過去時間的事實,任由法西斯思考加以撥用,同樣不是辦法。在全球化資本主義加速擾動世局的時代,回歸特殊性是防止真實災難的有效手段,但更要緊的是:回歸特殊性也要求時間與空間的距離必須維持,留下緩衝的空間,以免歷史「撞上時間的牆壁」。這樣的虛擬比電子通訊更徹底,卻也是一種形體的翻製,具有消除愚形,透過符號化來緩和經驗跳動的效果。也只有透過這樣的虛擬,文化傳統才能免於僵固化、形體化的限制,重新獲得開放性,成為不斷更新的一種方式。
關鍵字:民族、時間、災難、希望、記憶
Walter Benjamin's conception of history appeals to nachtraglichkeit as a historical force which separates immanence as conformance with the existent from transfiguration as pursuit of the true. This separation, in turn, points to a utopian dimension, an underside of time where futuristic intimations of hope inhere in memories of the past. This conception is taken up by Benedict Anderson who claims that the modern nation-state is made possible by the emergence of a sense of events happening in "homogeneous empty time," which, presumably, would free the nation in principle from the possibility of transfiguration through catastrophic intrusions of the past into the present.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 wish to reconsider this question and, through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alterity of time, to rethink how the idea of the "democratic nation," as proposed by Zhao Gang, may make possible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he particular and the universal.
Toward the close of the 20th century, when two works of fiction from Taiwan attempts to sum up decades of experience with the perverse aberrations of modernity in local society and politics, each recapitulates in its own way the Benjaminian theme of a constellation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The Ancient Capital" juxtaposes a serenely classical Kyoto with a fallen Taipei, calling forth personal recollections and patterns of historical recurrence to constitute
negating desire. The clinging to the past here expresses a ne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esent; the past is reclaimed not as some frozen image or immutable world to return to, but as the possibility to enter mutual renewal with the present. The City Where the Blood-red Bat Descended invokes an alliance between local magical practices and European demon lore to confront the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corrupt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 Although Satan is described as permanently present, the novel affirms that, since catastrophe strikes only in the present, in the form of the totally new, there is always a sense in which any hope for redemption will point to the past as a possible model of reversal which would present the old as intervention in the new. Thus both works seem to value shock, in the form of the intrusion of the past into the present, as a way to bring about new insights into a worsening community, a world on its way to predictable catastrophe.
Guided by such literary assessments of the status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placing them in the context of an ongoing nation-building project, we may be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see how the idea of a radically democratic nation may be developed. In this context, of course, a return to "the traditional" cannot mean the hardening of an open past into a non-empty "rigid designator" of the present. But, as Ernst Bloch pointed out long ago, neither can we abandon such human embeddedness in the particular and in the past to fascist appropriation.
A return to particularity would be an effective way to prevent real catastrophe in this hectic world of globalizing capitalism, but only if a distance, both temporal and spatial, is maintained, so that history would not be "smashing into the wall of time" but would provide a breathing space, a virtuality more radical than that of telecommunications, in which cultural heritage would be freed from fixated embodiment and regain its openness, becoming a way to out-new the new, to disembody and symbolically manage real shock by producing its mimetic replica.
Keywords:nation, time, catastrophe, hope, memory
為什麼大和解不/可能?/陳光興(43 民 90.9 頁 41-110)
本文從冷戰與殖民主義所造成長遠歷史效應的問題意識出發,企圖指出這兩個歷史結構性的軸線,在全球性資本主義的驅動下,多元決定了亞洲地區現代性的性質,在二次戰後各地社會造成了主導性的衝突與矛盾。這兩條糾纏的結構性力量所塑造出動態的情緒性感情結構被轉化成政治動員的關鍵力道,使得國家內部,地區之間,乃至於家庭內部產生分化;這種具有情緒基礎的感情結構使得個個層次的大和解成為不可能,也使得國家及區域內部的和平契機無法開啟。換言之,為求個個層次的和解與區域性的和平,不能只在脫離在地歷史的政治及利益層面來處理,而必須在情緒性的感情層次為出發點來面對,才可能逐步開啟和平的契機。
為帶出歷史情境中真實的情緒性感情結構,本文以〈多桑〉與〈香蕉天堂〉為主要分析焦點,企圖透過文本中的呈現來解釋台灣當前主流政治中最為核心但又不能直接觸碰的深層禁忌:省籍問題。〈多桑〉描繪的是本省人下層階級的苦難,〈香蕉天堂〉則處理了外省人下層階級的傷痛。透過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本省人主要受到殖民主義這條結構軸線的牽制,在日據起所建構的「現代化的日本、走向進步的台灣、落後的中國大陸」的階序邏輯,對於國民黨作為冷戰流亡政權與外省人作為戰敗子民沒有情感上的體認,而外省人則主要受制於冷戰結構的軸線,跟中國大陸的人一樣對殖民主義沒有身體性的認識,有的只是反帝反侵略的大敘事,對於日本殖民主義在台灣所造成的文化效應在感情上沒有理解,甚至蔑視;雙方甚至以自己的苦難經驗來置換看到對方悲情的可能性。因此,在主觀的集體情緒結構上,兩條軸線平行發展,沒有交集,雖然在客觀的歷史結構狀態中,本省人與外省人都活在兩條軸線的交錯重疊中。這兩種情緒結構間的差異,以對日本的想像之落差為中介,外省人對日本的記憶是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的八年抗戰,而本省人的記憶則是一八九五年被中國割讓給日本,至一九四五的光復,這種差異是當前衝突矛盾的情緒基礎。要能化解這種深層的矛盾則必須相互看到彼此的苦難才有可能走向省籍問題的和解。
扁政府的上台意味著本省人的出頭天,也意味著國共內戰的結束,更意味著重新面對台灣日據殖民地歷史情節與長期親美反共情節契機的到來。本文準確的理論性政治介入則是藉由指出省籍問題的複雜性,透過說出不可說的集體性歷史心理分析構造,來破解主流政治的族群動員與分化。
最後,從本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省籍問題糾結了全球性及區域性冷戰及殖民主義力量的運轉,不是可以關起門來解釋的,台灣問題至少糾纏了戰前的日本殖民主義、戰後的美國後殖民主義、國民黨反共親美的威權國家主義等,歷經一個世紀的法西斯統治,這些性質都是台灣主體性構造的成份,與南韓的歷史經驗極為類似,雖然其特定的表現形式有所差異。要能夠重新理解台灣主體性的構造性質,我們必須將台灣經驗放回亞洲區域與第三世界,透過與其批判圈的實質互動,才可能拓展新的認識空間,提出貼切於新歷史條件的解釋,也才可能促成台灣內部省籍問題和解,與中國大陸人民之間的善意互動,乃至於走向亞洲地區的和平。
關鍵字:冷戰、殖民主義、情緒性的感情結構、省籍問題、日本、大和解、現代性、多桑、香蕉天堂
Starting from the intersecting problematics of the effects of Cold-War and Colonialism, this essays attempts to argue that the convolution of these two historical-structural forces overdeter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iolent) modernity in Asia. In various national and social spaces, the dominant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are results of the structural clashes. These two entangled historical lines of forces produced and shaped local emotional structures of feeling, which, in turn, has become the emotional (more than material) basis for dominant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e. Ethnic politics and ethenic nationalism. The clashes occur within the nation, within and among the sub-regions, and even sadly within the family. The formation of the emotional structure of feeling has rendered reconcilliations on all levels impossible, not to mention creating new conjuncture towards regional peace. In other words, to quest for regional peace and reconcilliations on all levels and spaces, we could no longer buy into the mainstream political practices, which have been a-historical and purely 'self-interested'; instead, confronting historically shaped emotional structure of feeling, on the psychoanalytic terrain, is a way to open up new possibilities towards peace within the nation, and towards regional security and peace.
Keywords:Cold-War, colonialism, emotional structure of feeling, shen-ji, Japan, great reconciliation, Duo-san, Banana Paradise
回應與討論
「大和解?」回應之一/宋澤萊(43 民 90.9 頁 111-118)
我先說廖朝陽先生的〔災難與希望〕。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到〔古都〕讓他看到:「他們〔本省與外省〕的分裂形式並不是互相忘記,永不接觸的兩股力量的分裂,而是一個形象分裂成兩個平等的部分,隱隱地指向一個尚未來到的完整。至於《血色蝙蝠》讓他看到:「只要有了足夠的昇化,省籍獨特性的力量,例如與每一位人性悍衛者息息相關的受難者過去,就沒有理由不能成為救贖希望的一個來源,甚至是唯一的來源。」這種看法是很了不起的,我們對省籍之間的看法一定要有這麼健康的看法才好。......
讀陳教授的論文,使我獲益不少,他對〈多桑〉和〈香蕉天堂〉的分析真是精采,使我又到錄影帶店去借了多桑看一遍,增加了許多的啟發。唯一遺憾的是我找遍了彰化及鹿港的錄影帶店就是找不到〈香蕉天堂〉,最後放棄,不過陳教授的介紹文仍然讓我很了解劇情內容。陳教授提出了外省人及本省人由於在基本情緒/情感有差異,造成雙方的不能理解,「外省人不能理解本省人的日本殖民情結苦難,本省人則不能理解因冷戰而強制遷移的戰敗政權下子民的戰爭傷痛經驗」,他認為「從而認真的相互看到本省人與外省人不同軌跡的悲情歷史,調整原有認知差距,這可能才是走向大和解的起點。」這種看法是這篇文章的最大貢獻。我個人相當同意這種做法,並鼓勵大家如此做。
但是我也想替這種做法作一些補充:
首先,提到外省人及本省人不相瞭解,在台灣並不是每一世代都一樣,如果以嚴重性而言,大概多桑那一代最嚴重吧,可是美麗島世代及其以後的世代,本省人未必不瞭解外省人。以我而言,我比美麗島那一代小10歲左右,我今年49歲,又是讀歷史系,怎麼可能不瞭解外省人的冷戰下的悲慘遷徙經驗及反日本帝國主義的經驗?其實本省人戰後出生的人很多都能了解外省人的,因為國文課本、歷史課本整天灌輸外省人的近代悲慘史實,可說是到了洗腦的地步,千方百計要本省人向外省人認同就是蔣介石的教育目標。外省人編出來的中國歷史其實並不是全中國的歷史,而是外省人的獨特的歷史,他以自己的悲劇經驗構造歷史,使用制度化的暴力,強行把那套歷史灌輸進無辜的本省人的腦袋,我們怎麼不了解外省人?我看外省人不知道台灣人的日本經驗才是真的,因為課本沒教。其實不但外省人不瞭解本省人,本省人也不瞭解本省人,因為台灣史最近才在國中生的課程中才被教導。以我24歲為例,當時是1975年,我離開大學,念完了郭廷以的中國近代史,蕭一山的清史,背了不少的洛夫、余光中的遷徙流離的詩,我完全知道外省人的命運,甚至懷疑外省人的命運怎麼會這麼倒楣和不健康,我認為那些歷史簡直羞恥,導致我畢業後決定不再念中國史,我寧願念西洋史,只因為不讓自己陷身在挫敗的情緒中;對台灣的事反而知道得很少,大半對台灣的知識還停留在父母的口耳相傳裡。我想今天的學生也許比我那時要好些,但也好不了多少。所以我有個看法,與其要加強本省人認識外省人,不如外省人先檢討出一套比較健康的歷史,不要一開始就是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好像外省人就要概括承受近代中國人一切的恥辱,這很不好,會把人逼瘋的,把健康的外省人歷史拿出來,再教本省人認識,這樣對本省人、外省人都有益;而在另一方面本省人和外省人則要加強認識本省人的歷史,這樣才對!
其次,我想陳教授並不是說,本省人和外省人不能和解的原因只在於不相互暸解遭遇和命運而已。我個人覺得目前雙方不能和解的原因很多,譬如說政治利益擺不平和意識型態可以說是最嚴重的。外省人失去了政權,如何東山再起,這是外省人不會放棄思考的,如何動員族群力量,甚至製造幾個李登輝式的人物加以攻擊,適當挑起族群仇恨是必要的,每四年有一次選總統及選市長的機會,豈可放棄?謝啟大、馮滬祥都是很懂製造仇恨的高手,動不動就燒書打殺「媚日」的本省人,因此大和解怎麼可能?另外是外省人的統一意識型態,嚴重挑戰了台灣的國家安全,本省人十分有警戒心,不願意簡單就相信外省人,這鐵定是無法在目前和解的,因為任何人都不願意自己的身家生命和財產陷入險境,外省人不能老是怪本省人防著他們,這是生死存亡的問題,不是兒戲。所以我認為能不能和解尚須由多方面探討,總之歷史是多因的,遷涉廣泛,我建議將來可以專題討論。
至於陳教授認為促成雙方了解,我已說過我抱樂觀其成的態度,這是個很正確有建設性的做法。另外在文章後面,陳教授提出不要叫外省人的小老百姓承擔歷史的傷痛,和承擔不認同台灣的污名,我認為這是真知灼見。從主體的死亡這個觀點來看,沒有任何人有權力把外省人小百姓變成傷痛歷史的主體,迫使他們承擔莫須有的罪責,我覺得外省人可以起來在本省人面前申辯,告訴本省人不喜當罪者,甚至不要承擔任何近代中國的屈辱,以一個新人的姿態重生於世,我以為這樣比較健康比較好,也是我常常鼓勵外省人做的。
「大和解?」回應之二/朱天心(43 民 90.9 頁 119-128)
對於「1987」年以來外省人的失落這種近乎定論的看法,我大致同意,唯覺得仍大有細究的空間,例如我個人的失落就和族群的大多數人不同,同族群中又因為階級的不同(龐大的國民黨中下級軍人和極少數的權力及權力附庸者),失落的內涵也有巨大的差異,絕非「本土論述」中刻板化的單一印象——外省二代=外省一代=國民黨=既得利益,緣此公式,自然便有「外省人因台灣的民主化或本土化產生權力的失落感」的結論,但,在我長時間的觀察,這道公式的每一等號都是不成立的。例如為數最多的榮民,他們從來就處在台灣社經的下層,從沒坐享權力或與權力有什麼關係,沒有過權力如何有所謂權力的失落感?
那他們的失落感是什麼?我以為是一種「想像的價值與信念」。我且以二十二歲以前的我為例(好巧,與二十二歲之前的岩里政男差不多),國族寓意加眷村生活加黨國教育加父母輩強大真實的鄉愁……,這些交織而成的「價值和信念」內涵極其簡單、抽象、甚至可笑(從不同族群不同時空來看),很可能是口號式的「反攻大陸」,可能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可能是民族主義情感的「洗刷鴉片戰爭以來的近代史國恥」等等,很迂闊,卻也無比真實,很長一段時間(甚至到現在),是支撐他(我)們不計較現實真實處境而能生存下去的主要力量。這個支撐他們的「價值與信念」,'87年來逐漸被主流社會(因族群政治動員)所質疑、訕笑、污名、乃至踐踏,我以為這是大多數外省人失落感的來源。多年來,我一直想以此題材作種程度的釐清(權勢者的少數/無權勢者的大多數),尤其在十多年前看過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人事件」時,便十分吃驚同為外省第二代曾是好友的我們,看待現狀和歷史會呈現如此巨大的差異——雖有友人提醒我外部矛盾沒解決前千萬別輕啟內部矛盾——外省權勢者及其第二代,固然有權力失落感(如宋楚瑜),也有多年後對台灣歷史、人民心虛愧疚,並動輒代表所有外省人道歉的(如陳師孟),對於後者,我其實半點不反對他們替自己道歉,因為相對'40—'60台灣人民的困窘,他們曾有意識或無意識因父輩的權勢而得到較佳的發展成就,但,請代表他們自己就好,因為我只要思及14、15號公園拆遷時那一張張臉、每次過境香港機場難民盲流似的返鄉老兵、《香蕉天堂》裡的「門栓」……,我不覺得有任何人可以代表他們向「台灣」道歉,因為,我隱隱覺得,誰(歷史?)也欠他們一個大道歉呢。
至於屬於我個人的失落(若失落多少意味著「價值與信念」的鬆動),早在我大一並正值鄉土文學論戰時即已開始。論戰中,我既非站在鄉土文學主張這方,也非對立面,我天真單純的僅僅站在「文學」那一方,當然,從政治正確來說,嚴重站錯邊了(但這要好些年後才理解釋然的),處於論戰中的我,不明白對方為什麼那樣生氣,而且生氣的如此真實,若因此他們是對的,我豈非錯了;但我自省再三,也不覺有錯,那麼,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儘管如此,我並不願意像當時的很多友人立即下換信念,一夜之間像換手套一樣,我對這樣的方式始終不信任)我走了一條現今看來仍然愚鈍的漫長、岐路橫生的遠路,暗夜行路的苦苦摸索,我個人的「'87年的失落」,在之前的十年早已開始。
我甚至非常願意形容這長段時間好像是屬於我個人的一個自我放逐,一個救贖的過程吧!用一個比較感傷的說法,米蘭‧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時所用過的典故,昆德拉用希臘悲劇「伊底帕斯王」做典故,伊底帕斯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殺父娶母,因此釀成了全國性的災禍,等他知道以後,他刺瞎自己的雙眼,自我放逐而去。是的,不知道就是無罪是無辜的,我花非常長的時間,包括當然我在同時那個期間停筆不寫,在做我自己的刺瞎雙眼、放逐而去的旅程,包括我可能大量的在閱讀。我都還記得當初對我來講很有意義的,類似像姚嘉文、林義雄他們寫的《古坑夜談》,或是郭雨新的《虎落平陽》,或是許信良寫當省議員四年的《風雨之聲》,看張富忠跟林正杰的《選舉萬歲》,張俊宏的《景涵選集》,他和許信良談「中產階級」,彭明敏的回憶錄,和我所能找到的黨外雜誌……。
這個過程前後非常多年,其實到現在都還沒有結束過。所以真要說所謂的失落,我覺得最大的失落是這些年來,我的一次重要的啟蒙,或是再銘記(儘管這些來源,如前面所說的閱讀,大多僅只是民主的ABC以及很粗糙的知識論證),我從他們學到,再也不會用感情甚至信仰的方式去面對管他多了不得的信仰和價值……,但是教會我的這些老師們,先後丟棄掉這些他們青春和自由換取來,並啟蒙我輩的價值信念,例如十年前的首度修憲,張俊宏說「以前國民黨可以獨裁,現在為什麼就不行?!」……,原來他們教我們不要拜神,在意的並非膜拜的不理性,而是神祇不對,是對的神,是他們認為對的神時,神,是可以拜,是更要拜的。
台灣的(所謂)民主化一場,在場、參予過的我,最大的失落在這裡。
至於宋澤萊回應文中坦率並樂觀提及的省籍族群問題,我從不以自身也許可以置外或倖免便不加思慮,例如我的一些本省籍友人或有勸慰「那種說中國豬滾回去的絕對不是說你們這種人,放心,他們是說馮滬祥和那些不知今夕是何夕的老兵。」作為一個但凡還以知識份子(薩依德定義的)自期的我自己,豈會因為被講的是「門栓」們而不是我就放心過日子。
我太過多慮了嗎?(真希望我能像宋澤萊那樣樂觀),我以為我是有理由的,套句產業界現下流行描繪景氣循環的話,我還沒看到一隻燕子,春天還遠的很。
兩年前的九月三日自由時報副刊王溢嘉的專欄文章(他和稍後文中提及的張良澤都是我敬重的前輩),文末如下。「張良澤曾經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將來若把大陸作家遣送回中國,是否會有人在書頁上頭印著,僅以此書送給我的故鄉台灣。對童年在大陸度過的作家而言,這是強人所難,因為台灣並非他的故鄉,但對生於台灣的外省第二代來說,確實是個有趣的假設。」
我的一切努力,是希望(或曾以為)這樣「有趣的假設」根本不需發生,無論「假設宋澤萊被遣送回XX」,或「假設把張大春、朱天文、駱以軍遣送回中國」,都絕不會發生!謝謝大家。
「大和解?」回應之三/邱貴芬(43 民 90.9 頁 129-138)
對陳光興論文的回應...
1.為什麼大和解不可能?
為什麼大和解不可能?陳光興提出的主要論點是:殖民主義主宰了本省人的歷史經驗,冷戰則主宰外省人的歷史經驗,「因為生活在不同的結構中,殖民主義與冷戰這兩個不同的軸線製造了不同的歷史經驗,這些結構性經驗身分認同與主體性,以不同的方式在情緒/情感的層次上被建構出來。」(頁9)此外,不同的「日本情結」也是「本省人」與「外省人」對立的部分情緒基礎;外省族群在中國的抗戰經驗使得外省族群懷有濃厚的敵視記憶,而背負殖民歷史經驗的台灣人則展現被殖民者對殖民母國通常懷有的曖昧情懷,愛恨交加。根據陳光興的說法,「第三世界對於殖民者共有的愛恨情結vs.反日之為「中國」當代民族主體的關鍵元素。這個關鍵性結構上的差異,是以「日本」想像為核心的中介,對於日本態度的分野,是當代台灣「本省人」與「外省人」對立的情緒基礎,也是「台灣人」與大陸「中國人」無法相互理解的主因。」
我的看法基本上和陳光興上述的論點有相當大的歧異。我認為,陳光興的核心論點(亦即: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對立衝突主要因歷史經驗造成——前者的情緒基礎建基於殖民經驗,而後者的情緒基礎則被冷戰經驗主宰,這是造成本省和外省族群對立的主要因素,由於無法理解彼此的歷史經驗而導致對立衝突)以及連帶的對日情結等等看法並無法解釋本省人和外省人的衝突對立。在台灣談省籍衝突,我想不能忽視省籍衝突中的所謂「本省人」在歷史經驗上有不可忽略的世代記憶斷層問題。戰後出生的「本省人」和曾經有日據經驗的「本省人」的歷史經驗大不相同,殖民主義並不在他們的情緒結構中扮演如同陳光興所說的重要角色。冷戰反而是這一代台灣人的主要歷史記憶。陳光興的理論只適用於李登輝一代的台灣人和隨國民政府從大陸移居來台灣的外省人;戰後出生的世代,不管是被標示為台灣人或外省人,基本上都是在冷戰經驗中成長的。不同世代的台灣人有不同的歷史記憶和經驗。陳光興論文中所提出的「冷戰不太是本省人的主要歷史記憶」(頁26)頗有商榷的餘地。.....
在廖朝陽理論的基礎上,我們還要追問:差異來自何處?「特殊與普世性」的互動如何進行?歷史記憶在現實情境下的正面創意性挪用是以哪一種形式展開,方能開啟族群共存的希望?我不認為差異來自於陳光興所描述的歷史經驗和記憶的不同。我認為更關鍵性的差異來自於不同族群在台灣歷史過程裡所發生的「知識性暴力」所帶來的結構中所佔取的位置,以及個人對這樣的結構的認知和回應態度。我也認為,如果沒有帶進有關「知識性暴力」以及相關的「臣服的知識」的反思,所謂「特殊與普世性」的互動很容易只落入空泛的概念。
我對廖朝陽所提出來的有關歷史記憶的看法相當同意。我特別對廖朝陽所說的「最簡單的懷舊也含有部分烏托邦衝力,指向受壓迫者的真實歷史,但總是含有可以開發的,進步的文化意義」這一個主張感興趣。對歷史記憶的眷戀和懷舊往往被視為反動保守的論述取向。陳光興和廖朝陽的這兩篇文章卻不約而同的強調歷史記憶的積極意義,以及挖掘過去開展未來契機的可能。廖朝陽在論文裡深入談歷史記憶,反覆辨證歷史過去和文化遺產可能帶出的激進政治意義。召喚歷史不應只被簡單地視為反動盲目的懷舊,反可藉著時間的多層重疊帶出未來的希望。對過去的眷顧其實表達了想要介入現在形塑過程的慾望;換言之,過去和歷史所提供的並非只是凝固不動的世界,而是與現在互動,並藉此讓過去和現在都得以更新的可能性。廖朝陽認為,當記憶朝「非理性」靠攏時,往往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應,打斷時間並開展未來的可能(Liao 1999:23-4)。過去和「傳統」因此可能代表相當豐富的寶庫,提供「介入現在」的重要契機。
廖朝陽的論文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觀點,但是,我卻覺得這抽象的理論層次探討讓人意猶未盡。這些重要的概念在面對實際台灣種種問題時的演練情形究竟如何?我在一篇文章裡企圖把台灣庶民記憶涉及的「知識性暴力」問題和廖朝陽主張的開展歷史記憶激進面向的概念作某種程度的結合,以便較具體而實際地演練非懷舊式的歷史記憶召喚的可能方式和其激進的政治意義(邱貴芬2001)。有關台灣庶民文化和記憶,在當代論述中並不多見。不過,我認為,要探討陳光興所說的本省與外省人的衝突,以及廖朝陽所說的歷史記憶的激進意義,台灣庶民文化和記憶都是不可忽視的重點。
「大和解?」回應之四/鄭鴻生(43 民 90.9 頁 139-148)
「多桑」的英文副名是"A Borrowed Life"(借來的生命),廖朝陽教授引伸出來的一篇英文論文名為"Borrowed Modernity"(借來的現代性),這個「借來的」字眼很貼切,我們的現代化是借來的,缺乏自發性。自從我祖父那一代之後,活在借來的世界似乎是我們難以逃避的宿命,就如我們今天討論到的四部作品的題目。譬如「香蕉天堂」,香蕉原產地應該是中南美,天堂應該也是個現代觀念。而「多桑」的叫法,在我們台南家鄉並不曾聽到有人用過。小時候有一家鄰居頗為西化,他們的小孩叫母親作「媽咪」,相對於多桑的日本,這是美國式的。我的父母輩則要我們叫他們「爸爸、媽媽」,這也是現代化後了的叫法,而我的祖父母輩則仍舊要他們的子女叫他們「阿爸、阿母」,我也聽過有叫「阿爹、阿娘」的。這裡反映的情況是,借來的東西充滿著差異性與拼湊性,甚至在同一個時期的臺灣(其中台南人可能比較有那麼一點自主性)。至於「蝙蝠」的意象,就一個比較鄉土的、自然的觀點來看,蝙蝠其實是與人類相當親近的動物。甚至在台北都會,你也只要找個較空曠、有水有樹的地方,在黃昏的時候抬頭一望,就會發現很多蝙蝠在空中捕食蚊蟲。蝙蝠在我們這裡會成為一種恐怖的東西大概也是一種借來的現代性吧。
因此,如果說借來的現代性太多種,太缺乏自我,以致讓我們陷入無可避免的衝突,那和解的源頭恐怕要回到那個前現代與各種現代的交接點上,進行全面反思。從這個觀點來看,就不只本省外省要和解,受國民黨加美國教育的我這一輩要與受日本教育的父母和解,我們兩代也要與沒受到現代化洗禮的祖父母和解。
我個人與外省人的和解沒有問題,我妻子就是外省人。我與受日本教育的父母的和解也不成問題,雖然我曾怪罪過他們為何沒有教我講漂亮的臺灣閩南話,只會背著我用日語交談,然而就如安德森所期待的,我們兩代人還是較為接近。與前現代的祖父母的和解確實會是一個考驗,但是都已走到所謂後現代的今天,對我個人而言應該也是可以解決的,尤其是在學習用河洛話吟唱唐詩宋詞的時候。當然我很清楚那個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但我感覺到有個和解的情懷在心裡頭,在精神上不再踐踏他們,就覺得心安理得,不再怨恨,雖然這樣子就有點與安德森的期待背道而馳了。這是我個人的層面,但就整個臺灣社會而言,當然不會如此簡單,而將是一個大工程,需要各個層次的參與。
而且進一步說,不只臺灣內部要和解,兩岸之間也要和解,而受到現代化衝擊的整個亞洲,包括日本與韓國,也都有自身的以及互相的和解要求。其中很重要的一環是與日本的和解,不論是從臺灣出發,還是從大陸出發,只是去看到「日本」的侵略行為,要求「日本」道歉是絕對有偏差的,就如溝口雄三的質疑「一個國家的歷史全部過程就這樣成了其他國家的罪孽,這難道是可能成立的事」?我們也必須看到日本人其實也是陷入現代化的迷障裡,才會衍生出後來一連串的國族悲劇。因此就像陳光興的論文開頭提到的「漢城在集體哀悼韓國的現代性」,我們是必須把場景拉大拉遠,進行一種全面的和解,如此本省外省的和解才有可能,也才有意義。
「大和解?」回應之五/陳映真(43 民 90.9 頁 149-156)
正如同陳光興教授的《帝國之眼》和其他一些激發思考和爭論的論文一樣,〈為什麼大和解不/可能?《多桑》與《香蕉天堂》殖民/冷戰效應下省籍問題的情緒結構〉也是另一篇促人反省和再思的文章。
在我極其有限的學術論文閱讀範圍中,這篇論文是學術界第一次用「冷戰」、「冷戰構造」——這個自五年代開始就被廣泛第三世界和先進國內批評的思想圈用來分析事物的視角——的角度分析台灣的戰後的文化。此外,在論文的開章,作者大量引用了南北韓人民第一次在民族長期「分斷」五十年之後重聚的愛和愴痛的報導。我想這也是長期不曾以民族分斷的苦難意識為研究和思想射程的台灣學術界所罕見。再者,對於電影《多桑》和《香蕉天堂》的思想與審美分析,表現了作者對於影象思維的傑出的理解、感受和分析力。
正如作者所說,這篇論文的確開放了很廣闊的討論、補充與商榷的可能性,因此也在這兒做幾點回應:
1.關於冷戰與殖民主義的連繫問題
2.關於台灣「省籍矛盾」性質的問題
3.關於台灣人對日治歷史的現代性評價
4.關於外省人因「冷戰」(反共)而疏離,依戀故土;
5.其他
(甲)對於被意識形態「刻板化」(stereotyped)說法,例如日本殖民政策特殊(有成就,較為和善)論;「國語」對「台灣話」的統治論;殖民地現代化論(戰後台灣下層階級生活不如日據時代等等),似乎都還應該可以從具體的歷史與社會的細緻研究,撥開迷霧,補充新的材料。
(乙)對民族主義無區別的排拒。當代在台左派,不分省籍,大都批判中國民族主義乃至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之一般,而不區分豪強民族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與弱小、被支配民族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差別。面對布希的新軍事霸權主義的TMD、NMD體系和美日安保條約新指針、周邊有事立法等,面對新圍堵主義和新冷戰的陰風四起之時,亞洲進步知識份子在反對美國與日本戰爭政策和霸權主義上有共同的戰略。但在戰術上,美國、日本的左派當然反對自己國家的、擴張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中國、韓半島、台灣、菲律賓的左派;在受支配於新帝國主義及其威脅下,無區別地放棄和批判民族主義,豈不等同繳械!我們的問題,似乎是區別新殖民地精英的反共的、國粹主義的、扈從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右派民族主義,和人民的、反帝的、民族‧民主運動的民族主義,而反對前者、發展後者。此外,部分左派反民族主義的部分根源,是否與自己家族歷史和階級出身有關,也是一個研究課題。
一般論文
「外籍新娘」現象之媒體建構/夏曉鵑(43 民 90.9 頁 157-200)
經由分析媒體報導的敘事策略,本文解構了「外籍新娘」現象作為一客觀「社會問題」的合法性,指出「社會問題」是一種詮釋工夫,其形塑需藉用各種有效的敘事策略。台灣媒體透過相互抄襲的報導內容,輔之以官方說法、捏造的統計數據、模稜兩可的文句,將「外籍新娘」 現象定性為社會問題,其中女人的形象或為無可奈何的受害者,或為唯利是圖的吸血鬼,並常與外國人犯罪畫上等號;而跨國婚姻中的男性則被形塑為「社會所不欲者」:肢體或精神殘障、道德卑劣的騙徒與沙豬。除了媒體文本分析之外,經由行動研究中親身與媒體工作者交手的經驗,本文分析媒體建構過程的權力運作,指出媒體是新聞過濾器,產製過程即是消音的過程,因而提醒「事實」的社會建構是充滿權力鬥爭而非是人人可參與的詮釋遊戲。
關鍵字:外籍新娘、媒體建構、社會問題作品
Based on the narrative analysis of the media reports of the "foreign brides" phenomen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ocial problem" is a product of "interpretative work" accomplished by various effective narrative strategies. By overlapping media coverage, collaboration with governmental agencies, fabricated statistics and equivocal wording, the Taiwanese media construct the "foreign brides" phenomenon as a social problem. The brides are portrayed either as passive victims or materialist blood-suckers, and prone to committing crimes, while the bridegrooms are portrayed as the "socially undesirable," that is, physically or mentally disabled, and deceivers and sexists. In addition to the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media reports, my personal interaction with media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doing action research, helps deepen the analysis into the dynamic process of media construction, revealing the power struggles over reality construction. It shows that media is a news filter and the process of making the news is the process of silencing. It hence suggests that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is a power struggle rather than democratic interpretive work.
Keywords:foreign brides, media construction, social problem work
米酒加鹽巴:「原住民影片」的再現政治/林文玲(43 民 90.9 頁 149-156)
本文透過對於兩部阿美族影片的分析,一方面探討影片在它產出的環結中,影片參與者(包括影片拍攝者、被拍攝主體以及其他的合作對象)如何進行彼此意義的交換、協商、妥協和共構,以及這種種痕跡在影片中以何種方式呈現。另一方面,從影片文本與它企圖勾連的內外脈絡所提供閱讀的可能性,解讀兩部影片的身份政治、現代性和部落文化之間的諸多問題與關連。
從影片作為一種社會實踐,本文觀察到原住民影片影像再現所觸及的詮釋、溝通、翻譯和維護的議題和意涵:在透顯「原住民性」的同時,面對業已存在的定型化、本質化、固著的「他者」再現形象,作為一種自我書寫、自我刻劃的對抗性再現實踐,一方面為文化、傳統、部落社群、身份政治重新加以刻劃銘寫,進而對一直以來的有關原住民文化再現/翻譯的種種論述、意義系統及其內外環結重新加以提問。
關鍵字:原住民、原住民影片、族群文化、再現政治
This paper analyzes two Pangcai films in order to explore how,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these films and all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filming process(including filmmaker, filmed persons, and other participants)engage in mutual exchanges, negotiations and compromis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lms' meanings. How are the traces of these negotiations readable and meaningful? The paper further reads the two films' engagement with issues of identity politics, modernity and tribal culture, how these are variously interconnected and problematized in the contexts differently evoked in these two filmic texts.
Films are a mode of social practice, and this paper is interested in the questions of interpretation,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and advocacy that indigenous films and their representation strategies raise. As a form of resistant representational practice, indigenous films confront existing essentializing and fixating stereotypes as routine representational "other" in the dominant culture. In rewriting and reinscribing diverse and sometimes conflicting indigenous "selves", these films simultaneously question hegemonic discourses and sign systems that continue to construe and contain indigenous cultural representation/translation.
Keywords:indigenous peoples, indigenous film, ethnic cultures, representational poli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