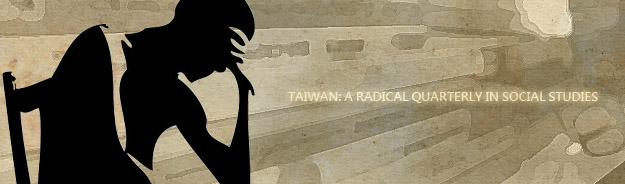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51期:
編輯室報告/陳宜中
國際貨幣基金報告曾指出,台灣政府積欠債務太多,若再不力求收支平衡,若繼續濫發公債,財政包袱將會愈來愈沉重。收支平衡、縮減赤字、量入為出,乃是新自由主義及「華盛頓共識」的金科玉律之一,不過,在健全政府財政的諸多方式中,新自由主義式的方案(為富人與資本減稅、縮減社會開支)卻是最不可欲的一種。在新自由主義的財政平衡論述中,出問題的、必須縮減的總是社會(福利)開支;至於政府放送給財團鉅富的財政利多,卻似乎從來不構成問題。
吳挺鋒的〈台灣財政平衡的現實與迷思:沒有平等的成長崇拜〉是本期「分配政治」專題的第一篇論文,旨在剖析台灣政府自戰後以來的財政調控模式的發展與轉折,並對新自由主義的財政平衡論述進行批判。按照吳挺鋒的分析,台灣當局從戰後到七年代末,所採取的是一種「生產至上的富國強兵」財政調控模式。表面上,此種模式交出了經濟成長與財政平衡的成績單,但在壓抑內需消費的同時,卻付出了值得嚴肅以對的社會代價,見諸於極小化的社會安全政策、選擇性與歧視性的社會保險體系、風險個人化的財稅制度設計,等等。自八○年代起,前述之調控模式因面臨經濟與政治的雙重自由化壓力而被迫修正。到了八○年代後期,一種新的財政調控模式開始浮現,而台灣的財政狀況亦開始出現戲劇性的轉變,從此走上了財政赤字快速累積的不歸路。吳挺鋒指出,直到一九九年止,台灣國庫的歲計剩餘高達兩千多億,未償公債餘額約一千多億,亦即這是一個還了公債仍有盈餘的無負債政府;但歷經了八九年的大幅減稅,以及九一年推出的六年國建計畫後,財政赤字從此一路往上攀升。究其原因,第一,在成長優先的意識型態下,台灣當局不斷對資本施以更優惠的稅式支出,同時為振興景氣而擴大公共投資,因此陷入蠟燭兩頭燒的處境。更重要的是,第二,自八年代末起,台灣財稅體制維護公平正義的再分配機能幾告喪失,而這是財政收入嚴重短缺的主因之一。在股市與房市空前飆漲的情況下,證所稅卻復徵失敗,土增稅改革亦胎死腹中。李登輝總統「過份強調公平正義是傳教士作法」的一席話,象徵著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因為大約從此以後,台灣當局肆無忌憚地向財團鉅富釋放財政利多,其大者如:九三年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九八年的兩稅合一、九九年調降金融事業營業稅、二○○一年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的修改、二○○二年土增稅減半、二○○三年立法院一讀通過調降遺產與贈與稅率,等等。這些財政利多使得政府財政嚴重失血,亦使得一般薪資所得者成為政府財政的主要來源。由於主政者既不敢得罪財團,又怕受薪階級跑票而不敢加稅,所以政府財稅收入佔GDP的比率逐年下降,目前已降到了百分之十三左右,只好靠舉債度日。
吳挺鋒剴切地指出,台灣政府債台高築的主因並不在於社會福利開支,而在於極不合理、極不公平的稅制。表面上,台灣的社福支出在九○年代持續成長,然而,除非我們放棄促進公平正義的財政目標,否則現今社福支出恐怕稱不上慷慨,而顯得相對消極。(在此,吳文所謂的「社會福利」不是為了政策買票而濫發的各種福利津貼,而是指制度化的社會保障。)在新自由主義的財政平衡論述中,政府對財團鉅富的利益大放送不算是造成收支不平衡的黑手;正因為這些利多使政府財稅收入大減,所以更必須秉持「量入為出」的原則,排除各種「不重要」的支出項目——尤其是社會福利開支。針對此一立場,吳挺鋒的回應是:台灣財政的病根並不在於主政者不懂得「量入為出」,也不在於社福支出截至目前為止的有限成長,而在於根本不懂得「量出為入」的基本道理,在於不去質疑現今稅制的極度不公平性及其所造成的財政短缺。在此,吳文呼應了近年來台社對社會正義的呼籲,及民主左派對公平稅制之基本理解:最核心的財政問題不是新自由主義者所謂的「量入為出」,而是「何種稅制才能營造出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
自九五年起開辦的全民健保,是台灣在九○年代的唯一一項重大社會政策。從社會正義的角度觀之,台灣的全民健保究竟有哪些成就與限制?什麼樣的改革才有可能進一步提昇其維護社會正義之職能?這些是呂建德在〈與弱勢者的團結——尋找全民健保中的正義基礎〉文中所欲回答的問題。他指出,在全民健保開辦前,將近有百分之四十五的國民被排除於一般公共健保體系之外,而必須自費就醫;全民健保的開辦使得絕大多數國民得以享有起碼且平等的醫療保障,因此無疑是一大進步。然而,就全民健保的收費方式而言,被保險人的所得能力愈高(低),平均保險費的費率卻愈低(高),因此對低收入家戶相對不利,亦壓抑了全民健保體系的重分配效能。整體來說,儘管全民健保的財務淨收支略具重分配效果,但若使收費方式更加公平合理,則重分配效果將更為顯著,亦較有利於社會正義之促進。在收費問題外,全民健保在社會正義維持上的另一大弱點,是對於失業者、不穩定就業者、低度就業者的保障不足。雖然政府全額補貼「低收入戶」的健保保費,但由於台灣的貧窮認定標準極為嚴苛,以至於符合補助標準的公民還不到總人口的百分之一。影響所至,許多繳不出保費的「新貧階級」根本被排除在全民健保之外,而這無疑是一項極為嚴重、亟待解決的社會正義課題。
董氏基金會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將近百分之六十六的受訪者認為「立法院建議行政院停止健保雙漲是合理的」,且有約百分之六十二的民眾表示,健保雙漲並無法改變健保的財務虧損問題。對此,呂建德的看法是,要有效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和不當使用,最主要必須從醫療供給面的控制著手;單靠健保雙漲這類需求面的控制手段,不但未必能達成減少浪費之目的,還使全民健保維護社會正義的職能逐漸萎縮。民眾自負額過高,當然會有抑制醫療使用的效果,但對低所得人口群卻非常不利,等於是進一步加重了他們的負擔,彷彿健保虧損全都是因為他們過度使用醫療資源所引起的。呂建德並不全盤反對部分負擔制度,他認為成本意識的缺乏確實可能會造成醫療資源的過度使用,但他強調,部分負擔不能定的太高,而且需要有其他的配套措施(如對收費方式進行改革),以遏止低所得者負擔過高的累退現象。
呂建德認為,若要使全民健保更合乎公平正義,同時避免嚴重的虧損問題,就必須設法從醫療供給面的控制下手,也就是對「醫療專業」施加民主控制。在目前情況下,衛生署與中央健保局雖以被保險人的代表自居,但其決策卻未必符合被保險人的最大利益。有鑑於此,我們有必要對目前處於一盤散沙狀態的被保險人進行培力,使他們的意見和需求不至於被排除在健保政策決定過程之外,而能夠真正獲得重視,並且對「醫療專業」構成一股制衡的力量。呂建德指出,目前健保政策的決策過程仍存在許多瑕疵,亟待一套能夠納入被保險人意見的「程序正義」機制的建立。倘若這類機制得以確立,倘若醫療專業的權力得以受到民主控制,倘若審慎判斷、理性對話能夠取代利益團體的尋租行為,則未來的健保政策應當會更合乎社會正義,而不像目前這般反其道而行。
洪惠芬的〈「照顧者正義」:性別正義不只是法律平等〉從近年來台灣婦女團體所推動的兩項改革(「民法親屬編」的修正及「兩性工作平等」制度的建立)切入,分析並詮釋這些改革行動背後對「性別正義」的理解及其進步意涵,並嘗試指出婦運未來的進步議程何在。貫穿這篇論文的主軸,是對「照顧者」與「養家者」之間長期以來不平等關係的批判,以及對「照顧者正義」概念的詮釋。洪惠芬指出,九年代婦女團體推動的「民法親屬編」修法行動,並不只是為了消除兩性在法律上的差別待遇,也不僅在於主張夫妻關係必須是一種兩個「平等個體」間的關係,還更進一步要求「養家者」必須與「照顧者」共同分擔所得維持與照顧的責任,而這意味著必須改善照顧者的經濟處境,使其獲得基本程度的經濟安全保障。對於照顧者處境的關注,具體而微地呈現在夫妻財產制的改革方向上。在新的夫妻財產制下,養家者必須把部分所得分配給照顧者,而這意味著夫妻關係不僅是兩個平等個體間的關係,還是一種顧及「照顧者正義」的「合夥」關係。
然而,就「照顧者正義」理念的落實來看,照顧者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並非僅透過婚姻制度的內部改革便能獲得解決,因其還涉及整個社會對照顧責任的看待與對待方式。如果家庭的經濟資源不足,則無論家庭內部如何進行經濟重分配,都還是無法扭轉照顧者、被照顧者或甚至養家者的惡劣經濟處境——遑論低收入的單親家庭;在這些並不罕見的情況下,對照顧者的扶助必得來自於家庭外部。洪惠芬認為,婦女團體所推動的「兩性工作平等」制度,不僅要求消除職場性別歧視及防治性騷擾,亦同時基於「照顧者正義」而要求雇主和國家補貼部分的照顧支出。例如,「兩性工作平等法」的第四章「促進工作平等措施」要求雇主必須對受雇者的照顧責任有所分擔,如提供育嬰假和家庭照顧假,縮短工時或調整工作時間等。不過,這些規定明顯是與企業界妥協之下的產物,因其只規定雇主必須提供休假,卻束手不管休假期間的所得損失問題;換句話說,似乎只有高所得或雙薪家庭的受雇者才有本錢放育嬰假,而育嬰假制度(至少直到目前為止)也因此淪為一種專為中上階層家庭設置的制度。到頭來,屬於中下階層的照顧者,似乎還是難以逃脫照顧責任所帶來惡劣處境——而這顯示「照顧者正義」距離其完全實現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依洪惠芬的看法,若要對「照顧者正義」有更圓滿的關照,國家就必須透過類似「照顧者給付」的提供,或「公共照顧服務體系」的建立,來部分地替代養家者原被賦予的供給者角色。
從洪惠芬的論文,我們還可以拉出其他一些重要的社會正義課題。與「照顧者正義」密切相關的是「被照顧者正義」。在台灣,至今仍沒有一個相對完善的長期照顧體系。此外,需要被細心照顧的嬰幼兒,可能因為家庭經濟條件不佳而無法獲得妥善的照顧與學前教育,但卻幾乎得不到來自社會的扶助——這種狀況明顯違反了「機會公平」此項社會正義原則。洪惠芬所謂的「照顧者給付」,在歐洲多半是以「育兒津貼」或「家庭津貼」之名發放的,而這似乎暗示著,在一般人的理解中,「被照顧者正義」似乎比起「照顧者正義」還更具有社會正當性。兩者間的關係為何,是否有所出入,又有哪些具體的現實意涵,無疑都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的重要課題。
「社會工作」是社會資源再分配機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自英國濟貧法時代起,社會工作者即被賦予了區辨出「值得幫助的」與「不值得幫助的」窮人的任務;時至今日,此種「守門員」的角色更已經從決定救濟金的發放與否,擴大到了如何「管理」弱勢案主的更多生活面向。王增勇的〈照顧與控制之間——以「個案管理」在社工場域的論述實踐為例〉一文,針對目前台灣社工專業中居於主流論述地位的「個案管理」,進行了傅柯式的微觀考察與批評,同時提供了一些宏觀的批判視野。王增勇指出,社工專業身陷於一種搖擺於「照顧與控制之間」的矛盾位置,一則無可避免地必須符合主流社會的期待,扮演社會控制與規訓的角色,另則矢言與弱勢案主站在一起,以其利益為優先——此種社會矛盾具體而微地呈現在「個案管理」的論述/實踐中。「個案管理」於八○年代在西方國家興起,呼應了英美新右派及全球新自由主義要求削減社福開支之政治訴求,被認為是可以有效節省成本、避免資源浪費的一帖藥方。由於台灣向來是美國學術專業的殖民地,美國專家所提倡的「個案管理」遂被引入台灣社工專業,並且逐漸蔚為主流。「個案管理」論述的引入,與社工專業嘗試改善與提昇其在專業體制中的弱勢地位有關,因此可以視為是「專業間權力鬥爭」的一種工具。但在台灣,引進「個案管理」的另一個重要脈絡是:因應社會福利民營化、多元化之要求,所帶來的監督體系的專業化需要。走民營化路線的政府部門,希望透過服務標準化的方式,建立起服務契約的監督體系,而「個案管理」就是政府定義專業水準的重要指標之一,並使得爭奪政府資源的民間團體競相學習「個案管理」模式。
然而,「個案管理」究竟是在管理些什麼?究竟是在複製哪些意識型態與社會邏輯?王增勇指出,在台灣,「個案管理」的論述/實踐,可以說是進一步強化了「政府財力有限,民間資源無限」的私化邏輯。以老人居家服務為例,「個案管理」似已淪為國家依孝道精神,對三代同堂家庭進行規訓的社會控制工具。此種「個案管理」的意識型態效果,是把照顧老人的責任「私化」成家庭(婦女)的責任,掩蓋了台灣長期照顧體系始終難產的制度性問題,並且合理化了社工員(代表國家)對「問題家庭」所進行的監控與規訓。
更進一步來看,「個案管理」業已變成了國家緊縮社會福利開支的一個重要工具。決定緊縮社福支出的政府找社工專家來背書,社工專家然後告訴第一線的社工員:刪減服務的政策目標是為了提昇社工員在「個案管理」方面的專業能力。此種說法不去挑戰台灣整體社會福利體制的嚴重缺失,反倒要求資源極為有限的社工員必須積極避免「浪費」,否則即是專業能力不足的表現。社工員除了必須扮演規訓弱勢案主的角色外,自己也變成了被政府與專家規訓的對象,而這整個規訓運動的目的又在哪裡?社工專家告訴社工員:刪減服務的目的,正是要刻意使弱勢案主的需求無法被滿足,因為唯有如此,才能夠激發非公部門服務與資源的產生,才能夠加快民間照顧部門的發展腳步——也才能夠使國家卸下沉重的社福負擔。在「社福民營化」、「福利多元主義」、「緊縮社福支出」的意識型態作用下,「個案管理」愈來愈像是當前台灣「反動的分配政治」的馬前卒。在專業化的「個案管理」論述/實踐中,關乎社會與分配正義的政治議題被忽略,甚至可說是被「去政治化」而從公共議題中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社工員的專業能力問題,或「問題家庭」成員互控不孝的家庭爭議。當前社經制度的種種缺陷隱而不見,而被「私化」成了家庭或個人問題。王增勇語重心長地指出,身為社會分配機制的一環,社工專業若不想成為無知的幫兇,便必須坦然面對自身處境的矛盾,並從反省之中尋找進步轉化的契機與動力。
以上是本期專題「分配政治」的四篇主題論文。這個議題對照於近年來台灣社會日益惡化的分配正義,可說是無比迫切,但在兩大政黨陣營的惡鬥中,卻只得到微乎其微的關注。台社希望能夠藉由對這個議題的重視,將分配問題提升到公共討論的層次,也希望——不揣淺陋——為批判的學術實踐提示新的問題區域。注意的讀者應該也可以從這個議題的推出,理解台社關注全球化議題後頭的規範性動力之一。以後,台社還將陸續推出相關的專題。
趙中麒的〈關於台灣原住民「民族」生成的幾個論證〉是對台灣原住民形成「一個民族」這個議題所牽涉到的幾個論證所進行的深入討論。趙中麒指出兩個重點:一、形成「一個民族」並非是以犧牲多元性為代價,反而它的正當性必須要建立在保存及發揚原先各民族的特殊性之上。所以,反對文化以及認同多元性的「單一民族」思維是要被質疑的。二、民族的建立不應只是「認同」問題的解決而已,而更是要以成為「法律上的權利義務主體」為最終目標。這可以理解為,原住民族也要積極的以公民的身份追求社會正義。這篇論文因此和本期的「分配政治」也有遙相呼應的關係。
跟讀者報告:從本期開始,台社將重新推出書評專欄,歡迎大家提供書評,中外文書籍均可評,但最好是和台灣以及區域現實或運動有關,以三千字為原則。本期有陳光興與馮建三的兩篇精彩書評,分別有關勞工運動以及跨國媒體。
這是《台社》第五十一期的編輯室報告。在未來的幾期中,台社將推出一系列的專題,包括籌組中的「激進地理學」、「醫學、帝國主義與現代性」、「中小企業與台灣國家神話」、以及「動物權」(以上皆暫訂)。這些專題都將由台社編委同仁擔當專題主編,組織文力,挑戰當代重要學術與現實問題。
媒體研究主題論文
台灣財政平衡的現實與迷思沒有平等的成長崇拜/吳挺鋒(51 民 92.09 頁 1-50)
本文透過歷史性的討論,分析戰後到1980年代的台灣財政平衡經驗,並批判地指出這樣的財政調控模式具有鮮明的反社會性質。但從1980年代起,由於經濟與政治的自由化壓力逼至,故使得原有的財政調控模式的危機叢生,並反映在不同稅源收入的消長與爭議上頭,而這也預告了新的統治權力結構的形成。最後,本文基於上述討論提出了一個展望性的結論,提醒台灣現今對於消弭赤字的討論與解決大多反映了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綱領,其效果不只是重蹈台灣過去的財政平衡經驗代價,同時更將惡化台灣的社會不平等。
關鍵字:財政社會學、財政調控模式、財政平衡、賦稅國家、稅式支出
Through a historical analysi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xperience of fiscal balance in Taiwan from the end of WWII to the 1980s, and finds that such a mode of fiscal regulation shows flagrant anti-social characters. From 1980s on, however, serious crises have appeared in this mode because of the pressing demands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This, in turn, foretold the formation of a new ruling power structure. Under such a structure, mainstream debates about fiscal deficit and its solutions mostly reflect neoliberal programs such as that in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Such a program may bring back Taiwan's past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fiscal balance, with the cost of worsening social inequality.
Keywords:Fiscal sociology, mode of fiscal regulation, fiscal balance, tax state, tax expenditure
與弱勢者的團結—尋找全民健保中的正義基礎/呂建德(51 民 92.9 頁 51-94)
本文探討全民健康保險的正義基礎。本文主張,全民健保現有的集中化制度設計可以達到維持社會基本公平正義的要求,儘管它仍存在著若干可以改善的空間。本文首先分析評估健康保險的三種正義標準,分別是私人配置式正義、社會正義以及程序性正義。其次,作者分析全民健保開辦迄今所達成的正義表現在那些方面,同時限制何在。第三,作者透過對於三種健康照護體系的比較,解釋了全民健保透過了那些機制能確保與弱勢者團結的社會效果。最後,作者分析全民健保仍存在著那些可以進一步改革的空間,並且指出目前那些改革建議可能是不利於全民健保維持基本社會正義的目標。本文的基本立場是健康是屬於社會正義而非私人配置式正義的範疇,因為在缺乏社會正義的保障下,任何追求個別人生目標的希望都將落空,因而健康權的保障是屬於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一。在此一關於社會正義的規範基礎上,作者批評了私人配置式正義的問題,分析了自一九九五年以來開辦的全民健保在維持社會正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同時也分析了其限制與不足所在。我進一步探討了全民健保做為一種「社會」保險,應該透過公共化的方式加以治理,以確保一個與弱勢者團結的機制,並且節制醫療專業的權力。然而,由於目前被保險人的自我組織力量仍然有限,因而必需透過若干制度性的措施維持程序性正義。
關鍵字:全民健保、正義、健保改革、台灣
This article aims to search the foundation of justice on which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NHI) is based.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NHI can fulfill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of social justice in the delivery of health care through its centralization structure. The author firstly discusses three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justice in the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private allocative, social and procedural justice. Secondly, the performance and restriction of NHI in maintaining the equal health status has been discussed. Thirdly, the author discusses why the NHI could be a viable vehicle for effecting 'solidarity with the disadvantaged' through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astly, some reform options for containing the rising cost have been discussed. Distinguishing between demand-side and supply-side reform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procedural justice matter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distributive and social justice in the NHI.
Keywords: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Justice, Health Care Reform, Taiwan.
「照顧者正義」:性別正義不只是法律平等/洪惠芬(51 民 92.9 頁 95-142)
本文將「性別正義」(gender justice)看待成一種社會批判的產物。因此,對於「性別正義」這個概念的定義方式,本文並非採取類似哲學上建立道德理論的途徑,對概念本身的內容作出嚴密的界定;而是從婦女運動這十多年來對既有性別現象所作的批判與具體的改革成果著手,去分析婦運團體、乃至整個台灣社會對「性別正義」這個概念所持的見解。婦運這十多年對社會所作的批判與改革遍及各個層面,但礙於篇幅的限制,本文將焦點集中在「民法親屬編」修正、和「兩性工作平等法」立法這兩項直接衝擊既有婚姻制度、及勞動市場性別體制的具體成果。從這兩項改革成果的的檢視與分析,我們發現婦運團體對「性別正義」理念的詮釋並不是用一般人所熟悉的「性別平等」原則就能窮盡的。對婦女團體來說,一個稱得上「性別正義」的社會,性別間的差別待遇當然是不容許的,除此之外,養家者與照顧者間的差別待遇,同樣不被容許存在。「養家者」(breadwinner)與「照顧者」(caregiver)兩者間平等待遇的落實,不應侷限於婚姻與家庭領域,還必須進一步地延伸至公領域。「養家者」不該只由男人來扮演,女人也該擁有這樣的機會;「照顧者」也是如此,因此男人也被賦予使用育嬰假、家庭照顧假的權利。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也不該將回應照顧者的「間接依賴」(secondary dependency)處境、與對照顧者貢獻的肯定,完全視為個別家庭的責任。從「兩性工作平等法」關於「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規定,我們明白:婦女團體仍舊期待國家能透過類似「照顧者給付」的福利供給制度,部分地替代養家者過去所扮演的「供給者」角色。不過按上面的分析,我們也發現婦女團體對國家作為「供給者」的期待要成真,顯然不是只透過法律體系的改革,就能達成的。它還意涵著一種責任間、所得間的重分配。
關鍵字:性別正義、照顧者正義、民法親屬編、兩性工作平等法、婦女運動
Since the notion of "gender justice" is the product of social critique, whose analytic definition is unavailable, it should be understood by examining how the women's movements in the past decade have transform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der phenomena and the meaning of gender justice as well. While women's movements have extended their critique and reformation to various aspects of social life, our discussion in this paper shall focus on two subjects: the amendment of "Family Cod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Gender Equality in Employment Law".
For the women's movement, the notion of "gender justice" is not exhausted by the principle of "gender equality". The feminist activists believe that a just society, i.e. a society of "gender justice", cannot tolerate the fact of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furthermore, the discrimination between "breadwinners" and "caregivers". The principle of equal treatment among "breadwinners" and "caregivers" applies not only to the sphere of marriage and family, but also to the public sphere. Men and women should have equal opportunity to be the "breadwinners", and to be the "caregivers".
The implications are: men and women should be equally entitled to parental leave and family leave. Furthermore, individual families should no longer be solely responsible for responding to the "secondary dependency" of the "caregivers"; the society must acknowledge their contributions and share the responsibility with them. If we look at the regulations for subsidizing employees' wage loss during parental leave in the "Gender Equality in Employment Law", we will understand that women's groups expect that, by providing the "caregiver's benefit", the state could get involved in the role of "provider" that used to be taken by "breadwinners". However, our discussion shows that such an expectation is unattainable simply by the reformation of legal system; it calls for the re-dis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ies and incomes as well.
Keywords:gender justice, caregiver justice, Family Code, Gender Equality in Employment Law, and women's movements
照顧與控制之間—以「個案管理」在社工場域的論述實踐為例/王增勇(51 民 92.9 頁 143-184)
本文針對目前社工專業居於主流論述地位的「個案管理」,以傅柯的知識與權力觀點進行微觀考察與批判。從社會工作專業所處的社會矛盾,「個案管理」作為一個知識論述,本身即隱含照顧與控制的內在矛盾。「個案管理」在台灣興起的歷史脈絡,與社工專業的殖民學術性格有關,廣泛支持的力量則來自於「個案管理」作為體制改革方案的保守性格、台灣社會福利民營化過程中國家對於管理機制的需求、以及社工專業自我追求建制化的動力。本文透過田野資料說明「個案管理」如何進入不同的場域中,形塑社會工作專業的專業自我、重組社工專業內部各個位置的行動者(政府官員、專家學者、社工員)之間的權力互動關係。結論指出以目前「個案管理」論述進入社工專業的運用方式,不但並未解決資源分配不均的困境,反而將社工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加以個人化,並使社工專業日益遠離其專業所承諾服務的弱勢案主。
關鍵字:個案管理、論述分析、社會工作
This paper critically examines the discursive practices of case management from the Foucaultian perspective. As a model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s, case management contains the paradox of care and social control. The import and rise of case management is supported by the conservative nature of case management as an option for reform, colonial character of social work profession, the needs for management by the privatization of social welfare services and the pursuit for professional status. The ethnographic data will demonstrate how case management discourse constitutes social workers' professional self, the tool for social control, and the object for regulatory power.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usage of case management fails to make structural problems faced by social workers visible but rather individualized. Its effect is that social work profession moves further away from its commitment to disadvantaged people.
Keywords:Case management, Discourse analysis, social work
問題與討論
關於台灣原住民「民族」生成的幾個論證/趙中麒(51 民 92.9 頁 185-224)
自1983年開始,由都市原住民知識精英所帶動的泛原住民運動促發了泛原住民意識之凝聚。1992年之後更因為部落主義的推動,使泛原住民族意識轉化為原住民各民族的意識,從而完成各民族的建構。然而,若我們武斷的認為台灣原住民的民族建構是一個斷裂的現象,將忽略了日治時期的番人,以及更早的部落在原住民各民族建構過程中所具有的連續性意義。從事後的(ex post facto)觀點來看,本文主張,在原住民各民族完成現代的民族建構之前,即分別以原型民族、初期民族之姿出現於歷史舞台。前者係屬在現代國家出現之前的部落社會;後者則是現代國家出現後,經過政策所動員的跨部落族別。後者與現代民族不同的是,她沒有民族主義所促發的民族運動。至於因為原住民運動所驅動的泛原住民族則是一種多元民族體,她的多元意義是由各民族作為單元民族體所補足。
關鍵字:原型民族、初期民族、民族、污名化的初期民族、原住民族多元一體
Since 1983, some educated indigenous intellectuals in urban leaded a pan-indigenous movement which stimulated pan-indigenou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fter 1992, tribalism as a new movement approach has shift pan-indigenous consciousness into the consciousness of individually indigenous nation and formulated individually indigenous nation. However, if we think the formulation is purely modern product, that thinking would be arbitrarily because of neglecting previous fanren (番人) and tribes as continuum of the formulative process. To the ex post facto view, I argued that there existed proto nations and incipient nations before the formulation of modern indigenous nations: the former involve tribes, the latter are the consequence of tribalization impelled by modern stat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ncipient nations and nations is that the letter have national movement stimulated by nationalism. Regarding "pan-indigenous nations", as a multinational unit stimulated through pan-indigenous movement, which meaning is supplemented by individually indigenous "nation".
Keywords:proto-nation, incipient nation, nation, indigenous stigmatized incipient nation, multinational unit
書評
主體形成的政治經濟學/陳光興(51 民 92.9 頁 225-230)
Colours of Money, Shades of Pride: Historicities and Moral Politics in Industrial Conflicts in Hong Kong(香港大學出版社,2003)是丘延亮從1985年起,用了十八年心血所完成的新作,雖然它所「記錄」的是短短十三天一群香港女工抗爭的歷史事件。
坦白說,這本書不好評,主要原因在它的書寫跨越了不同的文類與學術領域,它是人類學也是社會理論,是民族誌也是田野日記,是歷史也是小說,是中篇小說也是後設小說,是工業社會學也是社會史,是文化研究也是政治經濟學。Michael Taussig認為丘延亮創造了一種全新的sensibility,結合了說書人的藝術與社會理論家的鬼才。Gayatri Spivak將該書定位成資本主義理性的人類學,處理的主要是作用者(包括女工與研究者)的主體形成,總體而言該書是一個耀眼的展演(A vertiginous performance)。Ashis Nandy則認為該書是在挑戰社會科學的正典,取而代之的是大膽拋除專業主義的民族誌,這種特殊的田野觀察將工人所體現的社會知識本身視為一種工藝,一種志業,也成為激進異議份子對抗當代資本主義的新基礎。無論各家如何定位這本書,難以否認的共識,丘延亮在這本書中呈現了他自身的長處與特質:說故事,說故事是他一慣在很多場合中帶出問題的方式;我們無法否認的是他在主控說故事的方式及方向,往往會有他清晰、不隱藏其介入的痕跡,或是聽者會因為好幾條故事的線同時在跑,而有時無法體會以致於一頭霧水,但是他的故事都複雜而多面,不會完全因為主觀的偏好而消除異己的雜音。簡單的說,故事的複雜性反映了說書人本身腦子的複雜性。
評介《全球的好萊塢》/馮建三 (51 民 92.9 頁 231-)
根據美國電影藝術學院2003年的調查統計,除了少數當紅大明星外,好萊塢百分之九十九的從業人員,從跑龍套的臨時演員到缺乏觀眾魅力的二流影星,僅能過著三餐勉強溫飽的日子。
情勢如此,美國演員工會主席、女明星梅莉莎‧吉伯特(Melissa Gilbert)也就預計在2003年7月開始的新談判之前,先期與同病相憐的美國廣播電視演員工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levision and Radio Artists)嘗試合併,藉此增加勞方與資方的協商籌碼。這般的格局,集詭異與尋常於一身。
說詭異,是因為對內而言,好萊塢賴以繁榮的二極分化之基礎,竟然已經到了「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地步,對外而言,則大多數國家不免備受壓迫(其中,台灣應該是舉世受損害最嚴重的地方)。
說尋常,因為它內在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無論是以前的福特或近十餘年的所謂後福特彈性生產,勞方對受制於資本的感受,看來並無差別。早在近半世紀前的一本小冊子,鼎鼎大名的反社會主義的經濟學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就已經注意到,由於工作條件與螢幕的光鮮生活,落差太大,於是造成了好萊塢的一般工作人員,存在著一種「反資本主義的心境」。

